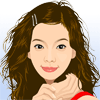 |
楼主(阅:9221608/回:0)90后已经有人开始服老
文:丹枫茶话
1. 好像在不少人印象里,90后们还是那个动辄到贴吧论坛里开骂、染着棕黄色头发、以在大街上骑弯梁摩托车为荣的叛逆青少年群体。 然而掐指一算,最早的一批90后如今已经27岁,混得好的话大概都是部门经理了; 哪怕是赶着20世纪的尾巴出生的人,如今也已经踏进大学校园。 无论怎样,都很难再和“叛逆”“疯狂”这些字眼儿扯上关系了。 尽管都还是二十多岁的大好年纪,但“变老”的迹象已在逐渐闪现,生活的很多细节,都不像过去那么鲜艳了。 从前会常去酒吧夜店,和同学在KTV里抢麦;现在话筒递到嘴边,却只是推诿地说句“嗓子哑了”。 从前下馆子,一定是无辣不欢,肠胃好得不得了;现在偶尔嘴馋了,忍一忍,还是拐进街角的粥屋。 从前骑一辆死飞车或者人妖摩托,风驰电掣没有目的地,只为耍酷;现在在路边随手推一辆摩拜,面无表情地骑到公司。 用中学生物老师的话说,曾经的我们都是“未分化的细胞”,拥有无限多种可能; 而如今,毕业的毕业工作的工作,选择越来越少,未来的可能性也越来越低。 最明显的一点,是对生活的想象正在迅速塌缩。 比如,十年前,大家的梦想是成为医生老师宇航员或者科学家;十年后,大家的梦想清一水都是挣大钱。 2. 2008年,我还在家乡的小城念初中,刚开始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些闲散的习作,引以为傲的阅读书目是小四老师的《悲伤逆流成河》和《左手倒影 右手年华》,青春期泛滥的荷尔蒙被加工成各种“疼痛系”“忧郁系”文字,恍惚间觉得自己有作家的潜质。 阿鑫是我当年的好友,于是我对他说:“阿鑫,我将来要当一个作家,去北京发展。” 当年,“全民奥运”的风潮吹遍神州大地,街头巷尾循环播放的一首《北京欢迎你》勾起了我对神秘帝都的无限向往。 开头那句“迎接另一个晨曦,带来全新空气”被我意淫了无数遍,觉得只要在北京,连喘气儿都能和别人不一样。 多年之后我终于来到北京,发现这里喘气儿果然和别处不一样。别人家的PM2.5指数是30,而北京,是530。 不过在初中孩子的眼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阿鑫坚定地表达了对我的信心,并表示自己想成为一名导演。 我跟他说,“导演也是文化人,你也得去北京。搞文化的人儿都要在北京。” 现在想想,那时候真是有胸怀有魄力,一无所有却迷之自信,总觉得自己是老天爷的宠儿,所有梦想的都能一个不落地实现。 阿鑫后来把这些特点归结为一个词:年轻。 3. 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开始变老了呢? 大概是从发现自己不再是社会上最年轻的那批人开始。 当TFBoys红遍大江南北,带着阳光微笑召唤你“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才猛然意识到00后已经强势登场。 就连最新一季《中国诗词大会》的冠军也是00后,各种声音都在不断地告知90后们:新货已就绪,请做好下架准备! 说得更直白点就是:你已经过了瞎折腾的年纪,放弃所有不切实际的念头,老老实实地接受生活给你的答案吧。 领导会让你把策划案打回重写,房主会提醒你又该交租金了,家人会逼问你什么时候结婚生孩子,每句话都像打地鼠游戏里的棒槌,瞄准了尝试向外探头的你。 突出重围的永远是少数,大多数人,只能束手就擒。 讨论的话题从偶像剧变成了招聘会资讯,烦心的问题从日本为什么要扭曲历史变成了三十块钱一盒的口罩为什么不包邮。 原来觉得年轻本身就是一种资本,后来才发现,要先有资本,才有资格年轻。 没长相没才华没存款,好像就连年轻的资格也要被剥夺掉。心怀梦想会被说成好高骛远,勇于尝试会被告诫no作no die,不想将就会被批判矫情浮躁。 所以只好节节败退,一次又一次地降低自己的标准,更正自己的立场。 最精明的选择似乎是:按照别人期待的样子活下去。 大一刚入学时,满脸不屑地说永远不会做公务员,绝不要过那种一眼看到死的生活; 大四毕业时,忐忑不安地报名国考,还专程跑到雍和宫去烧香祈愿,逢人便说公务员的好,又稳定、又安全、还有北京户口…… 从立志改变世界到低头跪舔世界,其实不需要太久,只要经历一次秋招就够了。 更可怕的是,在这个不断认输服老的过程中,对自己越来越不相信了。 潜意识里,已经接受了自己注定是个普通人,接受了一成不变的生活,甚至承认自己不配奢求更精彩的人生。这种为自己设限的思维的墙,偶尔想起,会觉得毛骨悚然。 4. 今年春节回到老家,找阿鑫喝酒。 算起来我俩差不多有五年没见面了,想象中的促膝长谈不醉不归,都没有发生。相对而坐,反而有几分尴尬,不知该从何聊起。 很显然我们都活成了自己没料想过的模样。 我虽如愿来到了北京,却再没想过什么当作家的梦想,每天在课堂上学习各种电路图结构图和波形图,下课后站在西三环的天桥上,看着脚下的晚高峰,开始考虑在哪里租房子更便宜,并能让我在一小时地铁内到达工作地点。 而阿鑫,他连北京都没来,还留在家乡的小城,给一家服装店打工。 聊过去,往事难在回头;聊现在,两个世界,毫无交集;于是只好一起聊聊未来。 我问他,打不打算自己开个店?他问我,是不是也要跟风考个研? 两个人,谁也不知道答案。相视无言,衰老的感觉前所未有的强烈。 记忆里的朋友们都变了样,男生的肚子越来越明显,女生的素颜越来越难见;自己好像走着走着就迷路了,找不到出发时的豪情万丈,深夜躲在被窝里辗转路在何方。 但还是要提醒自己,你是个年轻人啊!拿出点年轻该有的样子! 于我而言,可行范围内最大的“折腾”,就是在满满的理工科课表里,又强行塞进一节音乐选修课,以此证明自己还不是纯种的苟且,尚留存有一丝诗和远方。 选这门课的只有十几个人,女教授虽然四五十岁,但对音乐怀抱的热情依然像个十几岁的孩子,谈到贝多芬和莫扎特还是会激动得双眼放光。 每次见到这样的人我都会发自内心的羡慕,能有一件事业可以终其一生去热爱,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 更重要的是,因为这种热爱,身体里永远有一个部分是青春的,非但不会被时间击垮,反而历久弥新,越发闪亮。 为了让课堂效果更好,教授请来学校交响乐团的同学,为我们现场演奏卡农。 教室里空空荡荡,没有吸音墙也没有红地毯,但教授还是兴奋地说:“这就是室内乐啊!多么亲切多么精致。” 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课间时,教授和我们闲聊,说她其实今天心情有点糟,因为开车时发生了追尾。 “但是,不开心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至少还有音乐这么美好的东西可以让人享受。”教授说。 那一刻突然觉得,可能生活的基调原本就是糟糕的,是慌乱疲惫又无趣的。 你总盼着熬过这一劫后,一切就会好起来。后来才发现,它根本不会变好。 今天不会,明天也不会,永远都有糟心事。可就是在这一个又一个糟心事之间,会偶尔冒出一点小惊喜,一份小确幸。 就像茫茫大地,全是泥土,但别忘了,泥土里也开着可人儿的野花。 昨天,突然收到阿鑫的微信,他决定到深圳去闯一闯。 “挺忐忑的,”阿鑫说,“但更多的应该是兴奋吧。能跳出围困自己的旧圈子,好像重新找到了年轻的感觉。” 我跟他说,拜托,咱们本来就没老。 梅开腊月别样红 帖间广告位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