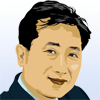 |
楼主(阅:81648574/回:0)中国汽车工业沉浮70年【上】
1987年7月,一个闷热难耐的夏日,一位七旬老人在一汽解放牌卡车30年纪念大会上,难掩激动之情:“我老了,无法投身中国汽车工业的第三次创业。但是,我愿意躺在地上,化作一座桥,让大家踩着我的身躯走过,齐心协力把轿车造出来,实现我们几代人的中国轿车梦。” 现场,鸦雀无声,台下的人们看到,他的眼里闪着泪花,他哭了,老泪纵横。 半个月后,这位老人在上海考察桑塔纳国产化项目时,突然病倒。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是:“同志们,我累极了,想睡一会儿。” 这位老人就是被称为“中国汽车工业之父”的饶斌。他曾是一汽、二汽的第一任厂长,和工人一起动手造出了解放、红旗和东风汽车。 20世纪80年代初,他牵头组建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在产业一线继续推动中国汽车业的改革开放。2009年,中国汽车产销量跃居世界第一,成百上千万台汽车走进中国家庭,饶斌那一辈的先行者没能等到这一刻。 在过去的70年里,中国汽车工业涌现出了无数个饶斌一样的汽车人。他们大多有着跌宕起伏的一生,几乎与新中国的汽车历史同构在一起——既为她贡献了一己之力,也因她而饱经风霜。在历史滚滚洪流中,他们的生命,似乎就是为中国汽车而来,为中国汽车而燃烧,哪怕最终像夜空中的流星划过,也在所不惜。 时光可以流逝,铅华可以洗尽,生命可以消亡,但一代代有名或无名的汽车人,对民族汽车的梦想却穿越时空,刻在车辙上,和新中国汽车工业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脉络一道,成为不可磨灭的印记。 1纸花、高粱、苞米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这注定是一个需要激情燃烧的时代。 1949年12月,毛泽东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专列。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争取援助。据官方记载,刚一抵达莫斯科,毛泽东就在斯大林的带领下参观了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看着生产线上一辆辆汽车组装下线,毛泽东对随行人员说,“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大工厂。” 这一句话,好似冲锋号一样,吹响了中国汽车工业在神州大地开创的号角。 三个月后,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即后来的第一机械工业部)组织成立了汽车工业筹备组,郭力担任主任,孟少农担任副主任,拉开了第一汽车制造厂筹建的帷幕。 1953年7月15日,长春市西南郊孟家屯,在一片曾是日本关东军残杀抗日志士的废墟上,万名建设者汇聚,六名年轻的共产党员抬着刻有毛泽东题词的汉白玉基石进入会场,伴随轰鸣的推土机马达声,中国汽车工业埋下了第一块基石。 随后,来自祖国各地建设大军,为建设新中国第一个自己的汽车工厂忙碌、奋斗。满载各类物资的列车和浩浩荡荡的劳动队伍在工地上沸腾,他们寒暑两季施工,在历史的空白处,一座座厂房拔地而起。 属于那个年代的激情和奉献创造出了奇迹。经过中苏双方的共同努力,仅三年时间,1956年7月14日,一汽生产的第一批12辆解放CA10型卡车下线,正式结束了“中国造不出汽车”的历史。 庆祝会后,400多名劳模、先进工作者,坐上新装配成功的解放汽车,组成报捷车队,与全厂职工见面,驱车向省、市委报喜。成千上万的人站在道路两旁,争先恐后目睹国产汽车的风采。人们不断向车队抛撒五彩缤纷的纸花,没有纸花的就拿高粱、苞米、谷子往汽车上抛撒…… 那是最纯粹的喜悦,不沾染复杂气息,饱含属于那个资源匮乏时代的民族自豪感。 2银龙、金龙、凤凰 解放牌汽车振奋全国上下,如萌芽一般,激发了中国汽车工业的成长。 解放CA10型卡车下线的同一年,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中间插话时说道:“什么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轿车来开会就好了。” 在这一号召下,经过一年的部署计划,一汽委派时任设计处处长的史汝楫和另一位工程师于1957年6月抵达北京,展开搜集国产轿车相关资料和图纸的工作。和新中国当时绝大多数起步的工业一样,开发国产轿车的条件堪称“四无”:无资料,无经验,无工装,无设备,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史汝楫在众多的外国轿车材料细细筛选中,找到了一辆法国的Simca Vedetti(西姆卡.维迪娣),并选中它作为参考车型。以这辆车为蓝本,一汽的设计师们做了大胆的设想和构想,保留车型顺利研制的同时,融进了中华民族的风格和特色,并为它设计了一条“银龙”造型的立体车标,后期还曾改为金龙设计,代表着民族象征。 1958年5月12日,带着“东风压倒西风”的寓意,代号为东风CA71的中国第一辆小轿车驶下了生产线,填补了我国轿车工业的空白,饶斌亲自驾驶着汽车,驶进中南海。 东风CA71在长春问世之后,不仅在祖国北方洋溢着喜悦之情,长江以南的上海人民同样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萌生了自己造车的想法。 上海造车有自己的底子。上海汽车厂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由德国宝昌公司建成,1918年归属英商利威汽车公司。解放以后整合为上海汽车装修厂,后改名为上海汽车制造厂。 不过,当时的上海汽车厂虽然有一些老牌技术人员,设备却严重匮乏,生产力极低,所以这次造车计划像东风一样,找了一个国外成熟车型作为蓝本。被上海汽车厂选中的是一台奔驰220S,当这台车运回厂内以后,包括上海底盘配件厂、上海内燃机配件厂在内的几十家最具实力的工业企业,都参与到了这台车的研制过程中,几乎每个零件都会有对应的部门负责研究开发。 经过半年努力,1958年9月28日,上汽的第一辆轿车样车装配完成,他们给它起名“凤凰”。车头凤凰造型的立标,也是为了和东风CA71车头银龙、金龙的造型相呼应。 和解放一样,东风、凤凰同样是序章中的音符,一款车,一座城,一个品牌,经典的故事不断谱写出新的序曲,时代的年轮缓缓向前,不断迸发出新的期望。 3红旗!红旗! 接过解放、东风、凤凰大旗的,是自诞生之日便饱含着更为强烈的民族情怀的红旗。 1958 年6月25 日,一汽团委书记王道义在传达团中央会议精神时,向与会的一汽人提了个问题:“能否在十周年国庆节前试制出高级轿车?” 当时,他们正为从北京传来的一个消息而苦恼:刚生产出第一辆井冈山牌轿车的北京汽车制造厂,又被委以重任——试制高级轿车,向国庆献礼。这个消息就像一池春水的涟漪,在一汽人的心中被一圈圈放大。 在这之前的5月,一汽采用“三结合”的做法,仅用6个月就试制出了我国第一辆轿车东风CA71,他们热切地期望第一辆高级轿车也出自自己的企业。 当天晚上,时任一汽设计处处长陈全召集大家开会讨论,憋了一肚子话的众人议论纷纷,观点出奇地一致:一定要把第一辆高级轿车的“第一”抢到手。这次会议上,他们还列出了时间表:7月末底盘设计科交出底盘图;9月车身设计科试制出车身。 一汽管理层的这种争先夺魁精神,一层层地感染了每一个一汽员工。说干就干,当年7月1日,一汽的高级轿车项目正式启动。 即便困难重重,所有人的积极性也很高,有条件上,没条件也上。一汽员工喊出了“乘东风,展红旗,八一拿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的口号。 高级轿车的研制难度远超以往。一汽这一次参照的蓝本是一台1955年款的克莱斯勒帝国,然而V8发动机的铸造难坏了一汽的专家们。 一生跌宕起伏的一汽轿车分厂原设计科科长、建筑大师梁思成的门生吕彦斌回忆,试制的最大困难是发动机,其中又以气缸体的铸造为难中之最。当时铸造的气缸体100件有97件是废品,但专家们还是百里挑一选出了几件毛坯进行加工,最终造出了V8发动机。 1959年9月,一个艰巨的政治任务落到了40岁的锻造车间主任陈子良身上。9月中旬,以他为组长,30名随车服务的同志将33辆红旗CA-72和2辆敞蓬检阅车分批发运北京。 35辆红旗轿车齐聚首都汽车公司,俨然成为一道别样风景。所到之处,引来无数市民观看,“红旗!红旗!”的呼喊声响彻天际。 岁月如虹,为国庆献礼的热血在无数汽车人心中沸腾,无论他们是否参与制造红旗,或者他们制造的车辆能否被幸运地搬到舞台中央,他们都在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助推中国汽车工业的前进步伐。 4特殊符号 在国庆十周年的阅兵式上,无论是红旗还是其他获得登场荣誉的品牌车辆,都提振了国人造车的信心,也为新中国汽车的规模“量产”铺下了基石。 但在走进寻常百姓家之前的那段岁月里,汽车和其他一些紧缺战略物资类似,在跌宕起伏的国家发展历程中,首先蕴意着一些特殊的符号。 1961年的冬天,北京格外冷。位于东郊的北京汽车制造厂内,工人们铆足劲,为的是确保一项特殊的任务能够按时完成。这项任务,不仅关乎到厂里每个人的前途,更关乎到军队战斗力的发挥,关乎到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 当时,中苏交恶,苏联已撤走了援华的专家和技术人员,解放军无法再从苏联进口嘎斯69轻型越野车。此时,国防科委交给北京汽车制造厂的任务就是设计制造一款轻型越野车,以解决当时我军面临的无车可用问题。 北京汽车制造厂首任厂长冯克回忆:“我们当时想的就是为人民服务,那时北京市委大力支持北京汽车的生产,决定把北京的一些小厂合并到北京汽车厂这个国营大厂里,像东四修理厂、正大喷漆厂等,同时集中了一批比较有名的汽车修理的能工巧匠,像膀子吴、膀子李等。” 工人师傅们参考了苏联专家留下的嘎斯69的技术资料,结合北京汽车制造厂多年来修配美国威利斯车型的经验,试制出了一款样车——BJ210C。 出于实战的需要,部队提出倾向于四门版车型,后排可以更方便地上下车。于是,北京汽车制造厂对BJ210C进行了改进和升级,推出了一款加长轴距的四门版轻型越野车,它便是此后火遍神州大地的BJ212。 之后,BJ212被定为县团级干部配车,加班加点地生产,仍然供不应求。北京汽车制造厂也因BJ212这一车型,开启了长达40多年的辉煌历程。 与北京汽车制造厂的风头正劲相比,直到1963年,上海轿车项目才得以重新启动,当时上海多家有实力的企业联合成立了上海汽车制造厂,原先生产凤凰牌轿车的技术人员也被请回了工厂。在全厂各部门的全力配合下,工人们终于在1964年2月生产出凤凰牌轿车的升级换代产品——上海牌SH760。 和红旗、BJ212类似,上海牌SH760也带着深深的行政印记。当时红旗等品牌车型有严格的配车级别限制,上海SH760的出现,填补了公务用车的空白。 以政府公务用车为主的上海SH760,实际上也面向普通百姓销售,不过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上海牌轿车并没有准确的售价,私家车也被看作是天方夜谭。但正如一位老汽车人所述,它为未来的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打开了一条门缝。 5怎样的拓荒者 1966年10月,37岁的刘书泽,背着包,拎着脸盆和鞋子,站在拥挤的列车上,对她将要踏足的一片陌生土地满怀憧憬。 一路上,她不停地转火车,从长春到北京,再到武昌,再辗转到丹江口,继而坐上了一辆破旧的中巴车,一路颠簸,终于到了鄂西北的一条山沟里——十堰。同一年,操着天南海北地方方言的数十万建设者们涌入这片山地间。 如今,已经90岁高龄的刘书泽,对当年看到的那一幕仍记忆犹新。 早在1952年底一汽建设方案确定之时,毛泽东就提出,“中国这么大,光一个一汽是不够的,要建设第二汽车厂。”然而,从构想变成现实,二汽的筹建却多费周折,反复经历“上马”和“下马”。 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防的需要,中央决定实施“三线建设”:在中西部的三线后方地区,开展大规模的工业、交通、国防基础设施建设,并且重新提出二汽建设。 这个重担又一次落到了饶斌的肩上。重担之重,超乎想象。经历多次难产后,直到1969年,第二汽车厂才在湖北十堰开工。当时苏联已停止对中国的技术援助,加之西方国家的严密封锁,我国汽车工业搞建设,只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 那是一群怎样的拓荒者?尽管多灾多难,尽管生不逢时,尽管条件恶劣,二汽的建设者如流浪儿般地赤着双脚走来,即便深感征程上顽石棱角的坚硬,一丛丛拦路的荆棘,泥泞的土地,依然坚持前行。 “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这是饶斌最欣赏的座右铭。作者/王慧
帖间广告位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