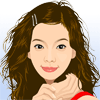 |
楼主(阅:72611328/回:0)埃尔多安的挫败?土耳其地方大选的得与失
3月31日,土耳其举行地方大选。此次选举意义非凡:这是土耳其2017年修宪为总统制后的首次地方选举,也是2023年总统选举前最后一次全国大选。选举结果出炉,埃尔多安尝到了惨胜的苦涩。 土耳其81大省中,总统埃尔多安所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P)虽仍维持多数统治,但只拿到39省的执政权,比起2014年的53省少了许多;更被共和人民党(CHP)连下三城,拿到了前三大省的执政权: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与伊兹密尔。 其中伊兹密尔本是CHP铁票区,输了并不稀奇;安卡拉虽是首次失守,却也还算面子问题;但输了伊斯坦布尔,那可就是实实在在的里子失血了,这里不仅是土耳其的经济重镇,也是埃尔多安政治生涯的起点,当年他就是以伊斯坦布尔市长的身分,一步步走到了今日的总统之位。 因此,为了“弥补”损失,在选举结果揭晓后,AKP甚至要求在伊斯坦布尔的32个选区重新计票。4月9日,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部分驳回了AKP提出的重新计票的呼吁。因此,虽然埃尔多安坚持认为,如果全部重新计票,结果也许会有所不同,但是最终还是未能改变其丢失伊斯坦布尔的结果。 但这次地方大选虽给了埃尔多安一计重槌,却也赏了他些许甜头,例如东南的库尔德诸省,AKP在这次选举中夺下了阿勒(Ağrı)、比特利斯(Bitlis)、舍尔奈克(Şırnak)三省的执政权,其中舍尔奈克更是传统的库尔德政党铁票区,会在这种地方胜选,或许连AKP自己都没预料到。 掌权十来年,埃尔多安凭借合纵连横的技巧、丰硕的外交成果、经济发展的荣景,树立起无人能敌的统治威望及魅力,成了"土耳其崛起"的代名词。只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经济问题正是此次的选举关键,这对埃尔多安与土耳其的崛起之路来说,都是短期难解的困境。 “苏丹”的合纵连横 埃尔多安2003年出任土耳其总理,之后连任三届,并在2014年成为土耳其首任民选总统,2016年经历了流产政变,2017年推动公投修宪,将土耳其改为总统制,更因修宪后的总统职权相当巨大,而被称为"现代苏丹"。 在国内政治上,埃尔多安成功瓦解常年干政的军方势力,终结了土耳其行之有年的"一国二君"制。自凯末尔推动西化以来,军方便自诩为凯末尔主义、世俗主义的守门人,并曾在1960、1971、1980、1997年四次干政,几乎每十年一次,且次次受民众肯定,因此过去还流传过一个笑话"土耳其不论谁当选,执政的都是军队"。 埃尔多安上任后,首先拉拢伊斯兰领袖葛兰,藉其宗教威望削弱军队在民间的影响力;随后进行多次"民主改革",其实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军队在文官系统内的影响力连根拔起,并架空多名军方高级将领的权力。 2016年土耳其发生了流产政变(但也有其自导自演一说),埃尔多安便更有理由整肃军队。结果证明,这波整肃的范围超乎想象,扩及学界、媒体界、司法界,上千所学校、媒体网站被迫关闭,十几万名公务员及学者被迫离职,埃尔多安的亲信集团随后取而代之。 军队的辉煌岁月一去不复返,而当初被用以制衡军队的葛兰,也因其宗教势力日渐庞大,俨然成了另一个平行政府,被逼流亡海外。埃尔多安收编军队,打压葛兰运动与文官体系,可说是弹压了所有国内的反对势力,故土耳其政坛上虽有反对埃尔多安的政治人物,但大多不成气候。 找回土耳其的东方身份 埃尔多安既在国内铲除异己,同时又靠灵活的对外政策为自己树立威望。土耳其地处欧亚之交,其身份认同也长年在东西之间摆荡。 凯末尔以降的土耳其领导人,多采欧洲取向的外交策略,积极加入欧盟,渴望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这样的失望已在历史中上演过无数次;而埃尔多安则象征了屡屡无所适从下的反动力量,其外交政策带有鲜明的中东色彩,并逐渐将土耳其的国家形象由西方侧翼转化为中东大国。 其首先介入叙利亚内战,在2016年的“幼发拉底河之盾”行动中建立了叙土边界的安全区,又在2018年的“橄榄枝行动”中取得叙利亚北部的阿夫林区,削弱国内库尔德反抗军的力量;而在以巴问题上,埃尔多安坚定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站在了政治正确的一方,并藉卡舒吉命案的新闻发酵来羞辱沙特阿拉伯,支持穆斯林兄弟会以牵制埃及,企图掌握伊斯兰世界领袖、中东强国的话语权。 然而即便埃尔多安看似回防中东,却也未全然放弃"西方国家"的身份,仍试图让土耳其成为欧盟的一员,且其虽改善与俄罗斯及伊朗的关系,却也不敢做得太过火,以免彻底激怒美国与北约。 埃尔多安的外交政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灵活摆荡,令土耳其人有种"重回奥斯曼帝国时代"的自信感,自然拢络了不少民心,构成其坚实的统治基础。 埃尔多安经济学的失灵 除了在整顿政治势力、外交场域中颇有建树外,埃尔多安也在经济上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然而其经济政策可说是肇基之初便危机四伏,并在一连串蝴蝶效应下,由荣景一片走向后来的货币危机,酿成了这次败选的致命伤。 埃尔多安的经济政策以低利率为主轴,辅以招揽外资、政府挹注基础建设等措施,令土耳其经济在过去十年内高速成长,其GDP在2018年时达到9098亿美元,世界排名17,人均GDP则达到1万美元; 此外政府也提供各种福利津贴,并大力改善各乡镇的基础建设,这也是AKP能在某些东南部库尔德省胜出的原因。库尔德人未必不想独立,但长年动乱下来,比起整天打游击的反抗军,能稳定供水供电的市政府显然更有吸引力,因此由独立转求自治,也逐渐成为某些库尔德人的政治要求。求取温饱,终是人之常情。 但既然赢了库尔德区,为何还会输掉前三大城?原因在于2018年的土耳其里拉崩盘与外债危机。土耳其的经济数据看上去耀眼,其金融体系却相当脆弱。经济过热导致通膨、资产泡沫、经常性账户赤字,而埃尔多安又时常与央行意见不合,强制插手金融体系,例如在选前强迫央行降息,以活络经济、促进建设等。 此举除严重打击金融体系的独立性外,也让经济过热得更厉害,长久下来,终于迎来了炸裂的导火线_——美国的经济制裁。 2018年特朗普将土耳其钢铝产品的进口关税升为两倍,里拉随即重贬20%,几近崩盘,接着便触发了外债危机,通膨率与失业率就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土耳其全国上下民怨沸腾。 对库尔德省的居民来说,政府提供水电是恩赐;但对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的居民而言,维持经济稳定是政府的义务。双方境遇不同,思考脉络也互异,因而有了完全相反的选择。 "土耳其崛起"该何去何从? 现美国虽已解除了制裁,但土耳其的经济也没能立刻恢复,仍是一片疲软,内伤颇重,从而波及AKP的选情。 埃尔多安或许选前就心里有数,经济问题会是自己的致命伤,故不断诉诸民族主义的选战策略,例如在竞选场合播放新西兰清真寺的屠杀视频,强调许多反穆斯林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人已混进土耳其境内,"他们应该要像加里波利之战的祖父们一样,被装进棺材送回去! 或大肆宣传土耳其经济崩坏全是欧美的阴谋,CHP是外国势力的走狗,"土耳其人千万不能向恶势力低头";以及听到特朗普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后,立刻愤而宣布"那我就让圣索非亚大教堂从博物馆变清真寺"等。 可惜这次似乎成效不大,经济疲软就像一把利刃,深插在埃尔多安政权体内,并让伤口不断失血,挑起民族情绪顶多就是上了层药,但刀没拔出,伤口仍在,药上得再多也无济于事。 而某些西方媒体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次大选象征埃尔多安的失势,且可能是土耳其走向"健全民主制"的起点,这或许有些异想天开了。 民众虽不满经济疲软,却未必会抛弃埃尔多安。埃尔多安上任后确实不断扩权,也压制媒体自由、铲除异己,但其一手打造的土耳其黄金十年,人民不可能全都抛之脑后、视而不见。 所谓"土耳其崛起",背后不只是华丽的数据,更暗藏了土耳其社会中被西化政策压抑许久的无声吶喊:伊斯兰认同、东方身份、欧亚强国等,埃尔多安未必全然奉行这些价值,但他让自己成为民众眼里的价值代言人,并把这些价值巧妙地镶嵌在政策中,成了土耳其崛起的舵手。 久而久之,只要挑战埃尔多安,就形同挑战土耳其主流价值观,也就等于挑战了土耳其崛起,这几乎是土耳其过往十年的社会氛围。这种集体潜意识不会因一场选举而消亡殆尽,也难因一次经济危机而发生逆转。 此次反对党虽有所成长,但民众几乎不怎么讨论其政见,多是为了"惩罚埃尔多安"而将票灌给另一方。经济问题虽然拖累了埃尔多安,却也没能将其赶尽杀绝,AKP仍取得了多数省分的执政权,稳住了土耳其的内政格局,国家各部也仍由埃尔多安的亲信掌控。 埃尔多安若想继续保有土耳其崛起的标签,首要之急便是改善民生经济,故或许会向国际货币基金(IMF)寻求协助,并减少对央行的干预。 但如此一来,便势必要在土美关系、土欧关系上有所让步,届时是否还能维持过往在欧亚间来回摆荡的外交弹性?恐怕相当不易。 或许此次大选真正挑战的,不是埃尔多安的执政正当性,而是土耳其现有的发展道路,是继续依赖外资与央行降息促进经济活络,进而在欧亚之间来回摆荡?还是为解经济困境,牺牲部分外交弹性,靠拢西方? 这不只是埃尔多安的个人挑战,也将是土耳其下一个十年的难解困局。文:刘燕婷
帖间广告位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