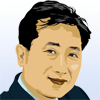 |
楼主(阅:86401278/回:0)季羡林:生活越难熬,心态越得好
坚定意志,苦练德语 刚到德国的时候,季羡林发现,不少达官贵人的子女也在德国留学,比起季羡林这样的穷学生,他们在德国的生活条件非常优渥,可是他们到德国留学更像是在度假,而不是学习。 到了德国以后,看到这些纨绔子弟令人厌恶的嘴脸,季羡林立下决心,一定要把德语学好。 这一群纨绔子弟,久居德国多年,唯一会说的德语,只有“你好”、“谢谢”、“再见”。他们常常逃课,只为四处游玩,更有甚者,常年流连于德国当地的声色场所。 他们在德国因为不守规矩闯了大祸,于是就在警察面前声称自己是高官的子女,在德国拥有特权,妄图以此将警察吓唬住。 季羡林虽然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外文系,但是,大学四年里,他与德语的接触,大多停留在书面文字上,少有机会能够进行德语口语的训练。 在柏林远东协会的林德和罗哈尔博士的帮助下,季羡林和自己的清华校友乔冠华一起到柏林大学练习德语口语。 德语教授名叫赫姆,季羡林在第一节课就认识到,赫姆是他见过最好的德语老师。赫姆教授不仅发音清晰,而且讲解透彻,即使季羡林是第一次听德语授课,他却没有一句听不懂的。 季羡林觉得,这不是因为自己的听力水平足够优秀,而是赫姆老师讲课的方式十分清晰透彻。 经过一个多月的强化训练,季羡林的德语口语有了显著进步,季羡林可以开始选择大学,修读研究生课程了。 一开始,德国学术交换处的老师希望把季羡林安排到哥尼斯堡大学。 这所学校汇集了许多德国古典哲学界的名师,但是,季羡林不喜欢这所偏远的学校。经过磋商,季羡林被派到哥廷根大学。 这时候,季羡林刚好遇到了从哥廷根来柏林办事的中国同胞,了解到格廷根大学的情况,想到将要离开自己不喜欢的柏林,远离那群纨绔子弟,季羡林十分高兴。 与梵文的奇妙姻缘 曾经留学日本的鲁迅,最瞧不起这样一类留学生,在国外,他们用老庄思想骗取博士学位,回到国内又用西方人的思想理论误人子弟。 季羡林到德国以后,始终没有忘记鲁迅的主张,他坚决不做鲁迅瞧不起的那种人,即使到晚年,季羡林仍旧坚信,真有本事的中国学者,会和西方学者争论他们的学问,并与国人讨论中国的学术。 刚到哥廷根的时候,他在朋友的建议下,试听了校内的希腊文课程,但是授课老师不仅讲课时候嗓音低沉,而且从来不向学生提问,季羡林一句话也没有听懂。 听课的时候,季羡林觉得自己如坐针毡,下课的时候,季羡林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学到。 一个偶然的机会,季羡林遇到了兼修梵文的中国留学生,想起在清华大学学习佛经翻译文学的时候,就有过学习梵文的想法。于是,季羡林先是向好友征求了意见,得到了好友的支持以后,季羡林决定了,要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 在清华大学时,季羡林就意识到,研究中国文化历史,离不开佛教文化历史的研究,梵文是佛教界创作佛经的时候所采用的语言,如果自己能够把梵文学好,那么肯定能够对佛教思想有更加透彻的了解。 梵文是格廷根大学的优势学科,很多语言学家都曾经在哥廷根大学从事梵文相关的科研与教学活动,正如季羡林所说,格廷根大学是学习梵文最理想的地方。 在国内,季羡林苦于没有机会学习梵文,走出国门,却有机会进入梵文研究界的一大殿堂,跟随梵文研究界最为杰出的学者们一起学习梵文。 这背后仿佛有一段奇妙的姻缘,季羡林曾经想学梵文,没有机会,如今摆在季羡林面前的,却是最好的机会。 梵文课的唯一学生 季羡林没有想到,不仅是自己有机会学梵文,而且,他还是梵文课上唯一的学生。授课老师瓦尔德施密特面对着这一唯一的学生,讲课时从无懈怠之意。 第一堂课,教授领着季羡林念字母,梵文字母非常繁杂,英文字母最多就发三个音节,梵文字母的发音音节动辄就有四五个,但是瓦尔德施密特教授的认真传授,让季羡林没有感到多大的压力。 季羡林坚信,既然有了一个好的开始,那么自己肯定能够舒舒服服地学梵文。第一节课,一直讲到下午四点钟才结束。 第一节课以后,季羡林以为往后的梵文课程,他肯定能够舒舒服服地上完,没想到在第二节课就受了当头一棒。教授对梵文的连声规律根本不加讲解,关于教科书上的阳性名词变化规律,也未曾提起,径直读起了书本后页的练习。 这些练习都是从梵文典籍中摘录的生僻词汇,不像现代语言那样一开始便能够学习生活日常用语,梵文大多脱离生活实际,理解起来颇为不易。 季羡林意识到了学梵文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于是他养成了课前主动预习的好习惯,个人的主动性被充分调动,下了课以后,他预习下节课要学习的知识,自己也逐渐适应了瓦尔德施密特的教学方法。 季羡林还在课后去研究所翻阅参考书,虽然这个图书室的馆藏不到一万本,但是却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梵文学者寄来的论文汇集,这些书在这里被分门别类,装订成册,大图书馆都没有的书,在这里却能轻而易举地看到。 瓦尔德施密特教授 瓦尔德施密特教授是季羡林的梵文老师,毕业于柏林大学,师从著名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他是研究印度佛教史的专家。而且,他还懂汉语和藏语,对于研究梵文来说简直如虎添翼。 在德国,大学教授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在学生面前多半会摆起架子。在格廷根大学,瓦尔德施密特会把其他学生的论文摔到地上,会骂他们的论文是垃圾,但是季羡林成绩优异,无所挑剔,所以在季羡林面前,他从来不摆教授的架子。 瓦尔德施密特上课不仅认真,而且很有耐心,季羡林形容,瓦尔德施密特能将梵文语法抠得很细,并且让季羡林完成大量选自梵文原著的练习题。 事实上,瓦尔德施密特对自己也很严格,他的两篇博士论文,实际上就是两本严谨的学术著作。这两本厚厚的大书,材料异常丰富,图表、统计数字应有尽有,令人看了眼花缭乱。 而且,两部书找不到半个错别字,那些稀奇古怪的字母和符号,他也能正确无误地运用。 说起瓦尔德施密特,他曾经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十几岁的儿子在上中学,二战爆发,父子二人都被应征入伍,爸爸成为军官,儿子则是前线上的一名士兵,可惜战争刚爆发没多久,教授唯一的儿子就死在了北欧的战场上。 尽管战争夺走了他的儿子,但是在季羡林的面前,教授从未表现过一丝伤心的样子,只是本来幸福美满的家庭,如今却显得寂寞与冷清。 教授应征从军之前,在大剧院买了不少演出门票,可惜无法退票,自己又没法陪同夫人,于是季羡林就在教授的委托之下,每周陪着夫人去看演出。 夜里,季羡林走在哥廷根的街上,不禁想起了远方的故乡,也正处于战争的水深火热中,此时此刻,内心一股乡愁,涌上了他的心头。
帖间广告位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