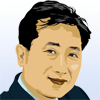 |
楼主(阅:69252197/回:0)全球史视野中的“永历西狩”【下】
三、缅甸:为什么成为南明政权最后的栖身之所? 九个掸族土邦,占据了大半个中南半岛。东吁王朝强盛起来后,四处征战。1556年,缅甸军队占领今泰国北部的兰那泰王国。兰那泰是通往暹罗和老挝的重要跳板,也是进入明朝领土的另一条途径。此时暹罗的阿瑜陀耶王朝和老挝都无力和缅甸抗争。莽应龙率军进入老挝本土,大肆劫掠,并夺取了明朝封给老挝国王的官印。位于老挝北方、在今云南省境内的车里国也表示臣服。缅甸的势力渗透到了湄公河流域。 莽应龙率军于1563年大举进攻暹罗,大败暹军,势如破竹。暹罗国王摩诃查克腊帕克被迫与莽应龙订立城下之盟,交出主战的王储拉梅萱等为质,向缅甸进贡,暹罗遂沦为缅甸的保护国。然后,莽应龙回师攻打兰那泰和老挝,前后共征剿了八次之多。1567年,莽应龙向暹罗国王摩诃查克腊帕克求婚未遂,勃然大怒,于是发兵进攻暹罗,所调动军队的数量竟然号称有90万之众。1568年11月缅军包围阿瑜陀耶城,1569年8月攻克。攻下之后,处死了暹罗国王。在进行了大肆劫掠之后,将阿瑜陀耶的臣民掠走,带回缅甸,只留下不到一万的居民,为之设立了傀儡国王。从此,缅甸对暹罗进行了长达15年的统治。 莽应龙死后,缅甸内乱。莽应龙幼子良渊侯(1600—1605年在位)保住了上缅甸半壁河山。继其王位的阿那毕隆(1605—1628年在位)又收复了下缅甸失地,并于1613年收复了被葡萄牙人占领的沙廉,把葡萄牙人驱逐出缅甸。他隆执政时(1629—1648年),缅甸又变得强大起来。 缅甸在向东扩展时,也积极北进,与明朝发生了长期而激烈的冲突。 万历十年(1582年)冬,投靠缅甸的中国商人岳凤带引缅兵及土司兵共数十万人,分头进攻云南西南部各地。万历十一年正月,缅军焚掠施甸,陷顺宁(今云南风庆)、破盏达。岳凤又令其子曩乌领众六万,突攻孟淋寨(今云南龙陵东北)。明军指挥吴继勋、千户祁维垣等率兵阻击,分别战死。这时缅王莽应里也“西会缅甸、孟养、孟密、蛮莫、陇川兵于孟卯(今云南瑞丽),东会车里及八百、孟良(今缅甸东北部,府治在今缅甸景栋)、木邦兵于孟炎(在今缅甸兴威以北),复并众入犯姚关”2。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底,缅军再次大举入犯,号称大军三十万,战象百头。云南巡抚陈用宾在加强边防的同时,派人联络暹罗夹攻缅甸,暹罗方面口头上答应了,但慑于缅甸的强大,未敢出兵。 从1584年到1593年,缅王莽应里连续五次发动侵略暹罗的战争。由于缅军主力用于对暹作战,因此对明朝的攻击减少了。从万历二十四年到二十六年(1596—1598年),中缅边境一度趋于平静。但是到了万历三十年(1602年),为了夺取孟密等地的开采玉石的矿井,缅甸出动十几万军队进攻蛮莫。土司思正力不能敌,逃入腾越求援,缅军追至离腾越只有三十里的黄连关。在缅军兵临城下、城内守军人少无力击退敌军的情况下,云南副使漆文昌、参将孔宪卿只得杀了思正向缅军求和。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缅军三十万进攻木邦,木邦失陷。此后,中缅战争才基本上停止。 由于明朝在战争中失利,明初设立的孟养、木邦、缅甸、八百、老挝、古喇、底兀刺、底马撒等宣慰司及孟艮御夷府均为缅甸控制,缅甸由此大大扩大了疆域。明朝人沈德符对此作了深刻的总结,说:“此后缅地转大,几埒天朝,凡滇黔粤西诸边裔谋乱者,相率叛入其地以求援,因得收渔人之利,为西南第一逋逃薮,识者忧之。…云南所统,自府州县外,被声教者,凡有九宣慰司、七宣抚司,其底马撒与大古剌靖安三尉,久为缅所夺,滇中可以调遣者,惟车里等五夷,并缅甸为六慰,与南甸等三宣抚而已。迨至今日,三宣六慰,尽入缅舆图中,他时南中倘有征发,严急不可,姑息不可,蜀汉之张裔被缚送吴,天宝之李宓全军俱覆,非有车耶?”3 由此看来,在中南半岛三个强国中,缅甸的武力最强,领土最大。如果永历朝廷要找一个庇护者的话,缅甸无疑比安南、暹罗更有资格入选。 1658年(永历十二年)年底,清兵从四川、贵州、广西三路猛攻云南。李定国督帅兵马分三路堵御,结果全线溃退,败归云南,请永历帝出逃。逃亡何处?朝臣意见分歧很大。沐天波建议西走缅甸,马吉翔和掌司礼监太监李国泰都赞同,李定国也赞成了这个主张4。沐氏家族受明廷之命治理云南,前后12代,为时264年。他们对主要邻国安南、暹罗和缅甸的情况都比较了解。李定国等人采纳沐天波的建议,并非没有道理。由上可见,“永历西狩”是李定国基于明代人对云南地区和缅甸历史与现状的了解而做出的选择。在当时的局势下,这无疑是最佳选择。 四、中国云南和缅甸:为何难以挽救永历朝廷? 中国云南不仅拥有支撑抗清战争的物质潜力,而且控制云南的李定国是一位优秀的军事领袖。黄宗羲说:“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败之。”5李定国拥有一支精锐的部队,成为抗清的主力。顾诚说:“李定国在…清初是抗击满洲贵族武力征服和暴虐统治的杰出统帅。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在明清之际各方面的人物当中,他是光彩四耀的一颗巨星,其他任何人都无从望其项背。”顾氏对另外一位抗清领袖郑成功则作了如下评价:“郑成功最大的失策是私心自用。……郑成功的复明是以他自己为首的‘明’,在西南永历朝廷明军兵势尚盛时,他决不肯出兵配合作战。”6这里姑不论顾氏的评价是否正确,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永历旗号下积聚的各抗清势力中,李定国是永历政权最坚定的支持者。这一点,对于仰人鼻息的永历朝廷至为关键。此外,与中国接壤的安南与缅甸两国,安南处于分裂状态,各政权之间相互混战,其中比较强大的后黎政权及广南政权到了1657年(永历十一年、清顺治十四年)左右,已对南明政权不太友好,而对南明态度较好的莫氏政权,力量又很微弱。与此相较,缅甸虽然也陷入内乱,但情况比安南还是好得多。因此,相对于其他选项来说,云南地区和缅甸确实是永历朝廷流亡时所能做出的最佳选择。 然而,这里要指出的是,在此时期中,云南地区和缅甸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云南地区在与缅甸的几十年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云南西部地区遭到缅甸不断入侵。缅军所到之处,“杀掠无算,大肆破坏”7,“三宣(宣慰司)素号富庶,实腾越之长垣,有险而不知设,故年来俱被残破,凋敝不振。”8沙定洲之乱则严重破坏了云南的东部和南部地区。云南南部和中部地区都被沙定洲占领,连省城昆明也被占领达555天。“(定洲)据省城,逐黔国,流毒两迤,先后死难者三十余万人。”9其部下王塑、李日芳攻下大理、蒙自后,“屠杀以万计”:。沙氏部队无纪律,滥杀无辜,抢劫财物,连黔国公府也被焚毁。由于战乱,云南已残破不堪,无力抵抗清军。 在缅甸方面,多年征战的结果,不仅使得国力消耗,而且国内各族之间矛盾日益尖锐。同时,缅甸政府的横征暴敛,连东吁王朝的立国之本阿赫木旦阶层也难以承受;,不少人卖身为奴以逃避徭役,步兵、枪兵、骑兵、轿夫等都有不少人负债累累,有的要求成为王公大人的奴隶[6]156。统治集团内为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也越演越烈。在17世纪的头六十年中,至少有3起王室成员的谋反事件[6]156-157。平达格力1648年继承王位后,情况更是江河日下。缅军在北碧被暹罗军队击败,暹军乘胜追击,兵锋深入到下缅甸腹地。1661年,缅甸发生宫廷政变,平达格力被杀,其弟莽白继位为王,混乱状态逐渐平息下来,但国势已难振兴。东北部重镇清迈被宿敌暹罗夺取。在这样的情况下,永历朝廷流亡到云南地区和缅甸,肯定不会得到预期的结果。 由于内乱,缅甸对永历朝廷流亡来缅也充满疑惧。永历朝廷逃到云南后,向位于中缅边疆的兴威<和孟卯(今云南省瑞丽)的土司要求提供人力和粮食。缅王平达格力得知,派兵帮助这些土司进行抵制。永历朝廷逃到缅甸八莫后,即被缅甸解除武装,安置在缅甸都城阿瓦附近的赫硁,寄人篱下,处境艰难。李定国得知后,和白文选分别率军进入孟定、孟艮、木邦一带,力图进行解救。1659年4月,白文选率数万军队进入缅甸,“杀缅兵四五万人”“缅人大恐”。1660年9月和1661年初,李定国和白文选又两次率军入缅“迎驾”,逼近阿瓦,与缅军大战于洞帕、象腿等地。三年之中,李、白部队几万人数次入缅作战,从阿瓦城下和远至南方的蒲甘的广大地区都遭到了破坏。这进一步引起缅甸官员对永历朝廷的不满[6]142。 1661年(南明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吴三桂率军攻下云南地区,随后率十万大军进入缅甸,逼其交出永历帝。缅甸此时无力抵御清军,只好同意引渡永历帝,以换取清军撤兵。次年,吴三桂在昆明篦子坡缢杀永历帝,南明最终灭亡。此时还在云南西南部抵抗清军的李定国,闻讯后悲愤成疾,于该年六月在勐腊病逝。至此,“永历西狩”的故事也划上了句号。 五、结语 传统的中国史研究有两大缺陷:第一,主要着眼于“中原”(包括黄河和长江两大江河的中下游地区)之历史。一个政权一旦掌握了这些地区,就成为历史的“中心”,其他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则是无关紧要的“边缘”,那里发生了什么,似乎对中国历史发展并无多大影响。第二,主要着眼于中国本身历史的研究。到了近代,由于西方入侵,中国史研究也随之重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但中国周边的国家与地区对中国的影响则被漠视。这些陈旧的看法,导致了我们对历史认识的偏颇。由于这种偏颇,像“永历西狩”这样的事件,在许多人眼中似乎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 然而,中国是由多个地区组成的,“中原”只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原”之外的地区的历史也应受到同样重视;其次,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不能把中国从世界中剥离出来,孤立地研究;除了西方,其他地区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有重大影响。 在“永历西狩”这个时期,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和发展,世界各地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费尔南德茲-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说:十五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从此以后,旧世界得以跟新世界接触,藉由将大西洋从屏障转成通道的过程,把过去分立的文明结合在一起,使名符其实的全球历史——真正的‘世界体系’——成为可能,各地发生的事件都在一个互相连结的世界里共振共鸣,思想和贸易引发的效应越过重洋,就像蝴蝶拍动翅膀扰动了空气”=。 由于全球化的进展,各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与此相伴的是纠纷也越来越多。作为解决纠纷的手段之一,战争也越来越频繁。与此同时,随着各国之间交流的增多,先进的军事技术出现后,也得以迅速传遍世界许多地区,形成全球性的互动。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军事技术的全球化”,简称军事全球化。因此可以说,经济全球化和军事全球化是联手进入“近代早期”的世界。这对东亚地区的政治、军事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这样的眼光来看“永历西狩”,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后隐藏着的大历史。“永历西狩”这件事本身,似乎不是一个大问题。一个没有实力的小朝廷,在华南和西南的穷乡僻壤东游西荡十多年,最后在许多人心目中的蛮荒之地的缅甸终结。在那些持有“中原中心”和“中国中心”观的学者眼中,这确实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然而,从全球史的眼光来看,“永历西狩”这一事件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皇帝流亡外国”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而且也在于这个事件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之覆灭和东亚世界整个格局的剧变,因此是世界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永历政权存在的时期,在中国和东亚世界并存着多种政治军事力量。如果把每一种力量当做一根线条,那么可以看到在当时中国以及东亚世界并存着多股粗大的线条。清朝方面,有入关的八旗(代表人物如豪格、多铎、孔有德等)、降清的明朝残余势力(如吴三桂等)和大顺军余部(如李成栋等)等;南明方面,有弘光、鲁王、隆武政权的残余势力(如瞿式耜、何腾蛟、张煌言、马吉翔等)、地方势力(如沐天波等)、郑氏集团、叛清拥明势力(如李成栋父子等)、由反明转为拥明的大西军余部(如孙可望、李定国等),等等。此外,还有西南地区的反明势力(如沙定洲等)、反复无常的西南土司势力。中国之外的众多力量也出现于这个场景。除了本文上面谈到的中南半岛三强——安南、暹罗和缅甸外,日本、葡萄牙等,都在这个舞台上显示了自己的存在。 南明政权建立后,多次向日本请求军事援助。著名学者朱舜水从弘光元年(1645年)起,曾多次到日本、安南、交趾(两国即今越南)、暹罗等国活动,前后十五年,历尽艰辛,终未成功,最后于永历13年(1659年)第7次到日本乞师未成后,决心不再回国,而定居日本水户。始终抗清的郑氏家族与日本有密切的往来,曾多次派人到日本“乞师”,还在日本寄存了巨量的贸易盈余,作为抗清的军饷。垄断郑氏与日本贸易的郑泰一人寄存在长崎的白银就有71万两之多[7]。 永历政权与葡萄牙人的关系更深。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隆武帝遣司礼监太监庞天寿偕耶稣会士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i)往澳门求援,葡澳当局对南明政权的请求十分重视,很快便征募得士兵300名,大炮数门,火枪一批,派尼古拉·费雷拉(Nicolas Fereira)为统帅,以耶稣会士瞿纱微(André-Xavier Koffler)为随军司铎。行至中途,得到隆武政权灭亡的消息。随后永历朝廷于1646年12月24日在广东肇庆建立,庞天寿于是转赴肇庆,带300葡兵事永历政权。这批澳门援军于永历元年(1647年)初抵达桂林,在与清军的战斗中起了一定作用?。永历二年(1648年),在永历帝倚重的大宦官庞天寿和传教士的劝说下,永历帝的嫡母王太后、妻子王皇后、太子慈炫都进行过洗礼,同时宫中受洗的还有嫔妃、大员以及太监多人。1648年10月,永历帝再次派人赴澳门求援,澳门的葡萄牙当局仅以火枪百枝相助。于是王太后决定派使臣陈安德与传教士卜弥格(Michel Boym)直接赴罗马向教皇求援。 这些都表明:诸多国外力量也介入中国当时的变局,形成了多条国外力量的线条。 上述国内外诸多线条中,有许多线条彼此之间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却都交织到了“永历西狩”这个事件上,因此“永历西狩”由此也成为这些线条相互纠结的节点。各种力量通过这个节点,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中国和东亚历史的大洗牌。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上述各种力量都代表着某种文化。例如南明所代表的是明代中国内地形成的“传统”的儒家精英文化,清朝代表的是加入了满族元素的“新”的儒家精英文化,大顺军和大西军余部代表的是中国北方农民的草根文化,华南和西南各土司代表的是各少数民族文化,安南和日本代表的是本土化的儒家文化,缅甸、暹罗以及老挝、掸邦代表的是南传佛教文化,而葡萄牙代表的是基督教中的天主教文化。这些内容和形式都各有特色的文化一方面彼此冲突,另一方面又相互融合,深刻地表现了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东亚世界文化的大变动@。 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曾说过:“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因此,现在被我们视为编年史的大部分历史,现在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辉照耀,将重新开口说话。”[8]阿里埃斯(Philippe Ariès,1914—1984)则说:“今天的史学家以一种新的眼光、以一种不同于以前的标准,来重新阅读那些已被他们的前辈们使用过的文献资料。”[9]事实确实如此。只要眼光改变了,同样的史料就会告诉我们不同的故事。因此,通过新的眼光,使得我们能够从“永历西狩”这个“小问题”看到“东亚历史大变局”这段“大历史”。
帖间广告位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