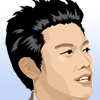 |
楼主(阅:82658973/回:0)中美贸易谈判的困境和出路【上】
一、从制度性安排讲起 1.双边贸易协议与最惠国待遇 中美1979年建交,但美国和其他国家与中国建交不一样,直到1980年才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一般所有双边贸易协定中,都有一个标准的第二条条款——签了这个协议,双方给对方最惠国待遇。唯独美国不太一样,在协定中多了一个承诺:现在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但如果将来中国加入一个多边组织,美国将按照那个多边组织的最惠国待遇给中国予同等待遇。这个承诺比别人前进一步,美国预计到中国将来会加入WTO(当时还叫关贸总协定)。这是美国当时做的一个承诺,也是后来它失信的地方,由此导致了很多的问题。 说到“最惠国待遇”,这里有两个插曲:
新中国1979年与美国建交,1980年有这样一个MFN待遇,正是这个促成了中美贸易的起步。为什么?因为当时美国的实施关税3%以下,如果没签这条,美国1929~33年的关税非常高,平均59.6%,这么大的关税差,中美贸易就会没法进行。有了这个待遇,中美贸易开始起步,而且一起步就比较猛。 2.中美第一次贸易战 当时中国能卖的东西说穿了就是最低级的工业品——坯布,福特总统在中美建交之后,给中美关系做了一个基本定位——中国是美国友好的非盟国。有了这个定位,外交和经济政策都按这个定位来,所以任凭中国扩大对美国纺织品的出口。 当时美国国内因为产业结构升级,纺织工业十分困难,因此美国与其他国家已经有一个“多种纤维协定”(Multifibre Agreement, MFA),各个出口国都受到出口数量限制,但唯独中国没有数量限制,因为中美双边制度就是MFA待遇条款。随着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的增加,这个问题最后到了临界点,中美第一次贸易战就从这里开始了。 但是,第一次中美贸易战的起因,是中国贸促会议副会长在香港做介绍情况的时候说漏嘴了,说我们当时的外汇是双重汇率:1.8兑1美金和2.8兑1美金。虽然大家都知道双重汇率的存在,但官方一旦这样表述,美国纺织工业界马上做出反应,指责中方汇率补贴,直接开始起诉。起诉之后中方当时没办法,但是中方的筹码就是双方的谷物贸易协议——为了解决国内几大城市人口口粮的问题,这部分必须进口,进口额当时是每年几百万美元。 这样,第一次中美贸易战开始了,中国宣布取消小麦贸易协定。我看到前两天关于中兴的报道就觉得好笑,和以前的套路一样,拿美国农民开刀,但区别在于:现在这招完全没有用了,因为美国经过WTO乌拉圭回合谈判,已经把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拉近了;而当时这招很有用,因为当时美国国内产品价格高,而国际上的农产品因为有补贴,价格极低,一旦中方取消谷物贸易协定,美国就很难了。 最后,通过谈判,达到了各方满意的结果。这个结局大家可能不知道,中国做了什么让步?因为一旦制裁,就足够把中国所有的纺织品驱逐出美国市场,所以中国说只要不通过汇率补贴制裁我,中方承诺:一,可以不对美国农民采取措施,二,答应加入多边纺织品限制协议,承诺美方可以对中国搞配额限制。 这是双方退步的结果,中国开始加入MFA的谈判,MFA是中国历史上加入的第一个国际贸易制度性安排,它是WTO和原来GATT中最差的一部分,因为WTO或关贸总协定主张自由贸易,第一条就是取消数量限制,而MFA是系统性偏离自由贸易的特殊安排,这是中国加入中美双边贸易协定之后第一场贸易战。 3.问题全面爆发 当时,我们基本上还是外贸垄断的体制,当时的外汇汇率是怎么制定的?大家都不知道,其实,我们是倒过来制定的——每年由外贸部核定出口商品,随行就市,能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按照基本成本来核定第二年的汇率,是这样一个做法,在这种情况下,出口的力度还是比较大,一系列问题就出来了。
也就是说,八十年代开始,中美贸易有了一定的制度安排,最惠国待遇条款加上一个多边数量限制,但到了九十年代,问题全面爆发,爆发的背景和八九有关系,八九之后,美国对中国原来“友好非盟国”的定位就松动了。 按照原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主任李洁明说法,中美建交头一个10年,是中国人牵着美国人的鼻子走,中国人比较主动,该怎么样怎么样,美国人真是适应中国人打交道的方法;八九之后,美国开始对中国进行全面制裁,高官不许接触。但是,它始终没有取消中美贸易最惠国待遇条款——美国国会每年都在通过这个协议,要取消这个待遇,但是美国政府心理相当明白,一旦取消这个待遇,关税跳到59.6%,双边贸易就阻绝了,中美建不建交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美国政府每年就这个问题都在阻挡,到什么程度?每年参众两院都通过的时候,美国总统就引用他的行政权利否决这个通过,而否决之后,参议院还有一个再否决的机制,只需要取得三分之二参议员的同意,因此,每年美国总统为这个苦苦挣扎,动用自己的政治资本与那些议员一个个私下做交易,让方案不要通过。但同时,它必须给业界一个承诺,证明中美贸易对美国有好处,非法转口、知识产权等存在的问题一定要得到解决。 4.突破制裁的多边谈判 由政治原因造成的双边制裁,累积到一定程度后,美国总统必须采取措施,通过经济来突破政治。老布什在处理中美关系、需要打开一个新篇章的时候,他做了一个两面的做法:一方面是破坏了原来对台湾军售协议,卖给台湾过时的战斗机,不管怎么样,过时的也是战斗机;另一方面宣布取消对中国的制裁。 在取消制裁之前,高官不能接触,于是多边机制很重要。像1985年提出了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借助乌拉圭谈判谈起来,八九后明面上中断了,但实际上是在多边场合谈中美问题,日内瓦成为中美高级经贸官员唯一一个会晤场所,旅馆基本上都是中国代表团。等到老布什一解禁,就可以公开谈中美问题了,当时对中国政府而言,面临的选择是要不要接受这几个协议,认真地在市场准入方面、知识产权方面做出一些让步,作为交换,让美国总统继续花政治资本去否决取消最惠国待遇的呼声。 在中美的谈判中,一开始也是属于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美国贸易代表负责双边的这些人,整理了很多美方公司看中方不顺眼的地方,只要开会,上来至少40分钟讲我们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中方当时谈判的班子是外经贸部美大司的,过去实际上是搞配额管理和补贴的司,它对边境措施WTO这些不了解,双方谈判时美方全面指责,这边要辩护的话,经济理由谈得不多,法律理由也不了解,所以最后毛主席语录都上来了。但既然谈判,就要解决问题,不能太过离谱,一个依据就是我们是不是参照当时WTO的基本方针和原则来谈:
这就回到了关贸总协定的五条基本原则上,通过这个开始谈判,于是谈判进入正轨。这里面涉及范围很广,中方也是换了几次谈判代表,最后结果还算不错,双方达成协议:中美知识产权的谈判,先于市场准入谈判完成;而市场准入谈判谈了很多方面的内容。所以,劳改产品等经过这个也做了很多改善,约束了内部,非法转口问题得到了遏制,纺织品对美出口在接近零增长的情况下继续进行。 这里也讲一下,其实,美国人在谈中国加入MFA的时候,对它的其他贸易伙伴是很不讲道理的,为了给中国配额,直接削减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配额,像台湾、香港、泰国意见很大。因为只要纺织工业界对中国的汇率补贴不撤诉,法律程序就要走下去,最后会导致中美贸易归零,为了让织工业界撤诉,美国政府承诺要让纺织品进口零增长,也就是不管你对贸易伙伴怎么样,总体要能零增长就行,为此,美国让其他贸易伙伴的纺织品对美出口,从增长变成负增长,中国变成了零增长。 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启示,虽然美国是提要求的强势国家,但为了达成中美贸易协议,即便动用手段也要依靠法律,由于唯一的办法是让起诉方撤诉,所以通过交换条件达到目的,结果是得罪了其他贸易伙伴,美国农民的利益得到了保障,中美关系可以继续往前走。 就这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贸易谈判不是坐在那里打架、喊喊口号就行了,不同政府受不同法律的限制,有多边的,有双边的,只能在这个框架内寻求解决,这里面需要复杂的谈判努力,不是像我们想得那么容易。 再讲一个中美双边谈判中的插曲,美国当时负责谈判的代表,对中美贸易也没有足量的估计,谈完之后挺高兴,表示如果达成协议,就能基本解决中美双边贸易80%的问题,剩下的20%,双边再解决解决就行了。这个观点在美国国会炸锅了,美国各界不接受这个话,中美贸易既有政治问题,又有其他问题,比如业界对中美贸易的期望——当时中国的外贸基本是垄断的,外汇国家控制,所以进入中国很难。因此,中美贸易没有那么简单过去的,而这个贸易谈判代表,就因为这么一句话辞职走人了,职业生涯提前结束,美国开始又一轮谈判。 市场准入谈判是一方面,这里再介绍一下知识产权谈判。在知识产权谈判上,中美双边的理念完全不一样,知识产权纳入多边谈判时,当初印度代表就说得很清楚,“我们的教育和你们不一样,知识产权是人类的共同知识遗产,每个人都有权用,你们那套没用,在这里没什么好谈的”,我们国家基本也是这样,没有基本的知识产权保护,而且对进口来讲,基本上要求一家引进,大家受益。所以这个谈判,一开始是理念完全不同,而且我们根本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谈判没有基础,推进非常困难。 但这个谈判下来,结果是帮助中国建立了一套知识产权保护法律,这个谈判其实是个双赢的谈判,没有这套保护的法律,我们现在的科研和发明根本不可能有现在这个情况,说穿了,知识产权保护是一手托两家:既要保证发明人的收益,让他能够有兴趣做这个东西,另外又有一个时间规定,比如十年以后到期,社会上大家全都能用。在中国宪法里面没有产权保护、更不可能有知识产权概念的情况下,我们把知识产权单独立法做了保护,这个是相当超前的,没有这个,很多东西不可能卖到中国来。这也说明中美通过贸易谈判,能够促进我们的立法,让我们向开放方向继续往下走。 5.什么是欧美强调的“对等”(reciprocal) 1992年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市场准入谈判,一系列谈判之后,中美双边的一系列东西就基本定局了,原来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再加上这些具体问题的制度性安排,一管就是25年,当初我们谈判也是做出了很大贡献。但25年过去了,这套协议已经不可持续了,现在一旦有贸易纠纷,我们还习惯于通过给美方一点东西来解决,比如去大规模采购,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错误:刚才我讲过WTO几个原则,其中一个就是reciprocal and mutualadvantages,这么多年官方都是翻成互惠,这个是错误的,reciprocal本身是对等,mutual benefits是互惠。这两个差别在哪里?我们过去不大注意这个差别,reciprocal在英语里面是个技术词,就是互相校验,你怎么样我就是怎么样,而且它不是“利”,它是谈的势,你有优势,我也有优势,和互惠互利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我们多年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原来的多边体制里有明确的规定,第四部分指出发展中国家不需要提供对等。但现在,特朗普明确提出要遵循“对等”这个基本原则。 前年欧盟对华政策进行全面评估,评估之后就完全调整对华政策,并且跟中国领导人知会了这件事,表示今后要对等,用了reciprocal这个词。但在六次最高领导那里谈到这个问题,中方反应都是互惠,没当回事,于是,欧盟方面觉得中方现在怎么这么傲慢,我们这么大的对华政策调整,他们表示根本就忽略!后来欧盟商会的头儿到布鲁塞尔来讲到这个问题,我说这个事搞错了,由于中方翻译错误,翻成了互利了,就把对等、把整个基本贸易原则全部忽略了,他们说原来是这么个情况,中方不是傲慢,而是没听懂。 去年问题开始严重了。特朗普上台后,去年2月1日发表首份国情咨文,随后原来美国所谓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朝元老、商业人士、美国商会主席,加上一些汉学家,他们组队一起发声,美国各大媒体都登了,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今后中美关系不能像以前那样,让中国人拿小利益、小合同一个领域一个领域来牵着鼻子走,中美关系今后必须建立在“对等”的基石之上,但是,这个新闻到了国内,翻译还是错了!这些日子打贸易战,特朗普宣布600亿的时候,专门讲了“我们要的是对等”,他觉得中方还没听懂,因为这个东西已经过来了,所以他用了mirror,就是镜子,要镜像。 实际上,在去年特朗普上台之后,我们很积极地组织采购、订单子,尽管特朗普那边全盘接受,但是这个问题还在。美方要求的“对等”,是“市场机制、竞争机制的对等”。 这个问题,我们有点听不懂,当然有听不懂的一方面,更有国内困难的方面:政府之前提出要建立公平竞争的国内市场,但这个活还没开始,市场要起基本作用,有一个竞争政策的问题,去年下半年,发改委开始搞公平竞争内部审查,但是美方要的可不是内部审查,要求的是对等,所以国内这一年多的努力没有太多地抵消掉威胁。 特朗普来访,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跟美国财政部讲了,说中方要开放金融保险,你们既然来访,咱们是不是一起搞一个新闻发布会,美方回答很明确,新闻发布会我们不用参加了,我们要求的不是单个领域的突进,我们要求基本市场竞争机制的对等。美国人一说话总是讲hinderUS commerce,你这个东西对美国的商业造成一些影响,这个commerce包括了货物进口的东西,也包括投资,也包括其他的服务条件,而这些服务条件,很容易就抵消掉削减关税的好处。无论是在美国的企业,还是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和独资企业,运营过程中都是有很多的抱怨,他就要求在市场竞争机制上完全对等。 最近,有些翻译好一点,“对等”这个词出现了,但是有些翻译还是翻成“互惠”:“互惠”是讲的可以数量化的好处,“对等”是讲市场进入条件和竞争政策方面,你要和美国接近,这个是新的要求了。 这个问题的理解还有待于中方下一步的推进,但中国国内比较难,因为我们有政府对企业的管理,有国企问题,有党建问题,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虽然不像过去那样分三六九等,但还是有行政操作空间,类似这些问题的改革比较难,也比较伤筋动骨。 帖间广告位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