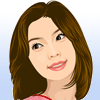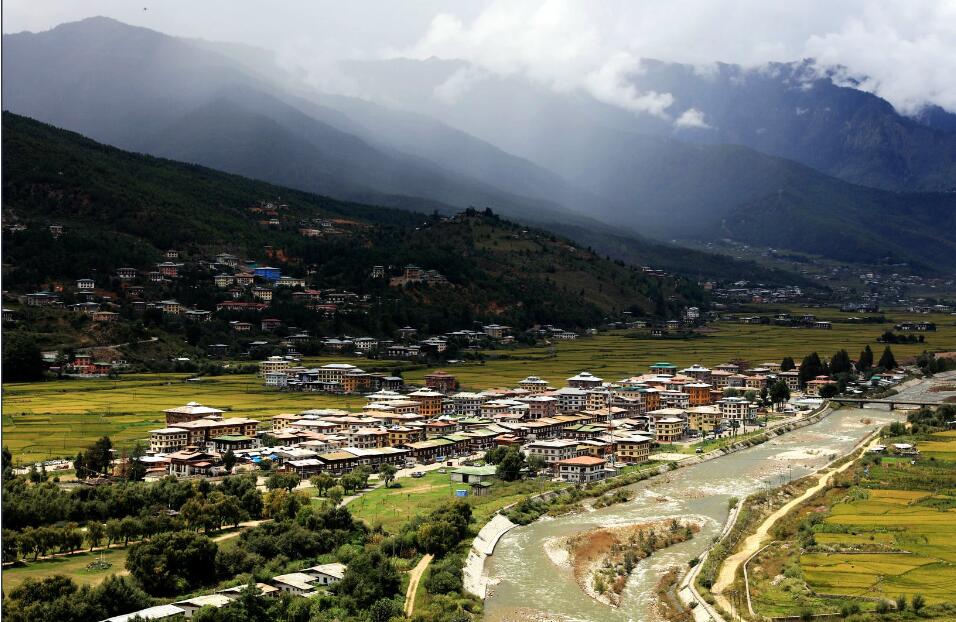
自小学开始,我便时常在家里对着书本上的字学写“大仿”,时间长了,自觉长进的我便忍不住“露试露试”,把写好的字粘在墙上。有一次母亲凑上来,盯着墙上的字看了半天后,对着颇有得意之色的我说:“我怎么看着你舅舅写的毛笔字,那些笔划有粗有细呢?”我闻言一愣,后来才发现,由于没有字帖和缺乏明白人指点,自己把毛笔字生生写成了钢笔字。再后来,随着笔法的娴熟和练习中的体悟,我愈发觉得母亲当时的那句话是书法之“法”,是对我最早的启蒙。
近年来,母亲更是偶有惊人之语。
有一次,母亲对我说,所有动物的名字,“人”是最好认最好记的。
“你看,”她手比画着,“就是往这一下,往那一下,就是人了,不像那些狗啊、猪啊、驴啊,要多麻烦有多麻烦,记都记不住。”
“所以做人一定得简单点,越简单越好,不然人就同别的动物没啥区别了。”最后她又说。
有一年,我陪她老人家登泰山。下山时,她问我:泰山为什么叫泰山?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来拜泰山啊?
我尽快搜罗大脑里有关泰山的知识:这山古时候叫大山,后来为了说明她比所有的山都大,就在大字上加了一“点”即“太山”,再后来人们取“天下安泰”的意思,就叫做了泰山。因为她在东面,被世人誉为五岳独尊,所以从古到今,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都会前来祭拜。
或许是母亲对我的答案不甚满意,说道:“我觉得泰山是咱中国人心中的神山,并且这泰山神是劝人积德行善的,能够来山上祭拜祭拜心里就塌实了。”稍后她又道:“心到神知!你看那些花大钱烧香烧纸和大把大把给神献‘钱’的人,其实不如下山把钱救济了穷人呢。泰山老奶奶是行善的,这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她老人家会稀罕你那点钱?”
话虽浅显,但母亲对泰山和神的认识较之我从书本上得来的更深刻。
我有个习惯,就是闲暇时翻看画册。有时候母亲也会随手捡起我刚丢下的画册端详一番。久而久之仿佛也看出了一些门道。一次,她翻开一本画册指着一张画对我说:“这个人画得好,颜色一点也不恶。既好又好看。”
一旁的我惊讶之极,鼓励她说下去。
“这画吧,我觉得好看和好不是一回事,有些画画得好看,可是觉不出好来,但是这个人的画让人觉得又好看又好!”这是她对张大千的评价。
我不得不承认,母亲的寥寥数语胜过了一些书画评论家煞有介事的宏谈阔论。
母亲的这些见识哪里来的呢?是源于她自小就名闻数十里的剪纸技艺,还是源于她的先天聪慧?
然而,母亲却是没有文化的,用她的话说,就是大字不识一个的“睁眼瞎”。
记得上小学时,刚刚读完一年级的妹妹,试图要解开一直埋在心中的疑惑,拿着语文书指着封皮上的字问母亲:你不识字是因为看不见这上面的字吗?母亲郑重地回答:我不是看不见这些字,而是看见了不认识。你们得好好学习,不能像妈一样当个“睁眼瞎”,不识字寸步难行啊!
参加工作后,一次用自行车驮着母亲去赶集,正在气喘吁吁爬坡的当口,远远看见水村的三大爷从对面走了过来,妈便从后面提醒我下车。我说,这正上坡呢,下来了再上就费劲了,在车上打个招呼算了。她不同意,硬是让我停下来,看着我给三大爷递上一支烟,又热乎乎地聊了一会儿,方才各奔东西。
谁知这事还没算完,回家后母亲沉着脸问我:“你今天没带打火机吗?”
“带了啊。”我答。
“那为什么不给你三大爷点上烟呢?”
我一时愕然。
上了大学之后,在小小的水村,我这第一个大学生或许在村民们的娇纵下不知不觉地自视甚高了起来。用母亲的话说就是说起话来老是我、我的。一次她郑重提醒道,你以后说话别老是我怎么样我怎么样的,你怎么了?你不就是多喝了点墨水吗,但论真见识比你的叔叔大爷们差得远呢!
母亲的絮叨中,我渐渐明白了文凭与文化是两回事,甚至见识与文化也是两码事。这就同钟表和时间不是一回事,而日头和时间也不完全是一码事一样。不然的话,你去乡下走走,那些老头老妪口中偶尔蹦出的土得掉渣的话会令你瞬间醍醐灌顶,那些充斥在农家院落里的乡情乡态,那些游走在人与人之间的扯不断的人情事故,那些氤氲在老百姓头顶上空的思想和感情,它们是什么呢?是文化吗?显然,它们是!
因了文化的原因,我在心里把人分为了四类:没有文化的文化人;没有文化的没文化人;有文化的文化人和有文化的没文化人。
诸位被我这颠三倒四的话弄迷糊了吧。
但我的母亲对此心如明镜!文/田庆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