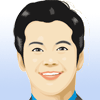 |
楼主(阅:9282369/回:0)其实每个人都想过死
文/杨熹文
一个姑娘在微信上给我写了一段很长的留言: 熹文,你知道吗? 作为家里的老大,他们总觉得我大学毕业后变化很大,思维方式很奇怪,就像大家都在准备结婚了,而我29岁了还没有男朋友,看起来也不着急,好像这世界只剩我自己了。 每年回家,都是一种变相的相亲。家里的亲戚介绍的男的,都是25,26岁,没读书的;还有一些比我大,我觉得自己和他们就像两个世界的人一样。 每年过年我都不想回去,好像我天生就比较冷血,离开父母后,从不会想念一样。今年家里发火,妈妈让我们必须回去,她在电话里说,谁谁又介绍了一个,等我回去了就见面。我很烦这样的场景,好像我长这么大就是为了嫁给一个人,然后生孩子一样。 可是,我也很理解父母的担心,我现在年纪这么大了,可是工作什么的没有一样是稳定的。前两年他们总是劝我考公务员,说考上公务员以后就有保障了,也会找到一个好的对象,一切都会好,可是,我考不上。现在我觉得无路可走了,想好好准备考公务员的时候,发现已经没有什么岗位可报了。 现在的公司,工资2500,保险什么都没有。我从毕业后,就一直在这家公司里,感觉自己一直在堕落。我们老板也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虽然我有不能离开的理由,可是我根本没办法再在公司待下去,家里人一直在劝我考公务员,可我心里不是那么想,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越靠近30岁的时候,我越害怕,现在自己跌落在泥潭里,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很多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活着有什么意义。 然后,她说,“我想到了死。” 我认认真真地想过死。 二十岁的时候,“大哭一场”就能解决的问题,突然间在二十六岁时即便哭上一整天也没有用了。 二十六岁时,我经历一场甩开膀子的奋斗,有好的男友,拿到了绿卡,也终于做上了喜爱的工作。生活正如我“预期”的那样一点点好下去。而如果我愿意,肯付出多一点的努力,我的生活还会更好一些。 人怎么可以在这个阶段不合时宜地想到死呢?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突然引爆了那样的绝望。 我曾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啊,我甚至比很多男孩子还要坚强。身体上力大无比,马达一般,心理上坚定乐观,从不放弃,就连我在冬夜里饿着肚子省钱都从未觉得绝望啊,而在那终于熬到了可以去任意一个餐厅吃饭的时候,我却变得生无可恋。 我也曾经是一个多么容易开心的人啊,一杯咖啡,一本书,去海边走走,都可以使我在精神上保持愉悦。然而二十六岁的那个节骨眼上,我喝咖啡,读书,去海边走很多的路,却没办法再让我笑一下了。 是的,那么坚强那么容易开心的人,偏偏在最该活下去的时候变得活不下去了。一切发生得非常突然,我突然觉得活着没意思,突然不再对任何事情感兴趣,突然不再有期待,也突然找不到什么动力。 新西兰著名橄榄球球星John Kirwan在提起年轻时的抑郁经历写道,“我知道我的生活看起来很棒,但我觉得真正的我与别人眼中的我是大有不同的。”他的直觉告诉他要“逃走”,而他差一点真的就在一次关键的比赛中逃下场。 我的潜意识也在叫我“逃跑”。我起先是拒绝社交,渐渐拒绝出门,最后连走路连张开嘴都觉得费力,有个网友在形容这种感受的时候说到,“像是泡在福尔马林里的一个死胎”。 这真是个恰当的比喻,我成为一个行走的被福尔马林泡发了的巨大的死胎。有一些必须的会面,我坐在桌前,同人讲话时,眼神是飘忽的,耳朵也关闭了,所有的思考都越过眼前的人,飘去了远方,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的灵魂不在这。 后来的情况更糟,有几次在早晨醒来,眼睛刚刚睁开,我就发现自己在哭,我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了。 为什么哭呢?我不知道。 又似乎知道,预感这是很多很多年来积聚的压力,正以最缓慢也最具威力的方式爆发。 太痛苦了。 我开始喝酒,起初我为自己夺回了一点开心,但这开心是有代价的,不久后我便不断地加量加度数。那几个月内我试了很多好酒,它们那么好喝却也那么无用,不能根治的绝望。整整三个月,我哭出来的都是酒精。 我不停地哭,男朋友拉着我的手。乐天派的他对一个人突然变成这样感觉非常不解,“我该怎么做,告诉我该怎么做?你要吃寿司吗?你喜欢那个玩具吗?你想不想去海边?” 我摇摇头,我说我想去死。 我说着话的时候我没哭,我是认真的。 不是像十几岁因为学业的压力,用小刀小心翼翼地割手腕又停下来的那种威胁式自杀,是认真地从网上查找着每一种死亡的方式,上吊是会有排泄物的;安眠药需要医生开处方;割腕的话很痛苦,只有等到失血过多才会死…… 我的痛苦令我变得自私,我甚至都不想去考虑生活中还有没有必须活下来的理由。那段时间我处于封闭自我的状态,不停告诉自己,我要干净而体面地走,就像我活着的时候那样,我要尽量不去麻烦别人,就像我活着时那般乖巧懂事。 我的男友后来和我说,他有多么害怕多么矛盾,多少次我哭着说“要一瓶酒”,他一边出门给我买酒,一边害怕一个小时后酩酊大醉的我会做出傻事。他说自己这辈子没有遇见过什么伤心事,我的抑郁是他永远也不能忘记的伤口。 我冷静得令自己害怕,以至于几个月之后,我在回新西兰的飞机上重温电影《无敌浩克》,我最爱的爱德华·诺顿有一只手表式的测量仪器,过高的愤怒指数会让他变成绿巨人。几个月前的我又何尝不是这样?那时我的手上也有一只隐形的测试仪器,抑郁掌管着表盘上令我随时崩溃的指针。 就在那次飞行的几个月前,我记得自己在高速上以100km/h的速度驾车,忽然想撞向对面车道上驶来的那辆卡车;在超市里买红酒,突然就想砸碎那一墙的酒瓶子;站在街上,人来人往,阳光正好,我却突然想哭出来。 而那趟回国之行,旁人说,“你还像从前一样,一点没变呢!” 彼时我从二十六岁跨入了二十七岁,过去那半年里,没有人知道我的生命里发生了什么。 但我知道我自己必须记得。 我的老同学们在回忆起我十八岁的时候,都很慷慨地说,“你热情、聪明、很快活、什么都不害怕……” 然而当我回忆起自己的过去,我可以老老实实地讲“我自卑、蠢笨、懦弱……” 这些都是真话,没有半点掺假,我一直把这些性格保存在身体里,只是如今才敢于把它们赤裸裸地显现出来。 而十八岁的自己,非常擅长伪装,害怕成为人群中的异类,才拼命用“满脸堆笑”去扮演“热情”,用私底下“两倍的努力”去获得人前的“聪明”,用“不要让别人瞧不起”的心情去逼自己表现得“很快活”。 所以当旧日朋友对我说起近来的抑郁,抱怨“有时真的想死”,而我也回应她说“我也想过死”的时候,我听到电话那端破了喉咙的惊讶: “啊?什么?你那么快乐的人?” 我们都以为其他人过得很快乐,但每个人都有情绪低落甚至是抑郁的时候。 事实上,当我和身边人聊到生活,很多人都有过极度不开心的时候,虽然没有严重到发展成抑郁症,但这种心态已经影响了基本的生活。 在我所接触的朋友中,无论是公司高层、普通白领、在校大学生还是全职主妇,很多人反映自己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生活突然间变得没有动力,没有意义,自己来到了一个非常奇妙的维度,已经无法再重温过去为梦想拼尽全力的回忆了,面前只剩下一道峡谷裂痕。你隐隐约约地预感,跨过去,对面就是全新的世界,跨不过去,此生就停滞在这万丈深渊中。 我后来是怎么好的,过程非常地艰难,在360°全方位地剖析了自己的人生后,我终于得出结论,我不是别人口中那个“热情、聪明、很快活、什么都不害怕”的人,我是一个自卑的,蠢笨的,懦弱的人,我必须要卸下所有包袱,和真正的自己面对面。 我没有经历过任何治疗,甚至都没去心理医生那里,现在不能说是完全回归到从前非常容易开心的状态,但大体上精神还很积极,该跑步跑步,该游泳游泳,该会朋友会朋友,有令我非常开心的事情,也偶尔会为一些事情短暂的难过,情绪基本稳定。 一位读者跟我倾诉,自己的姐姐患了很久的抑郁症,每天卧床不起,只是哭。她们全家试过各种办法,医生开的药也吃了很久,姐姐却始终没有好起来。直到有一天,读者给我留言,“姐姐好了,起床啦!说要去旅行!” 这更证实了我的想法,脱离抑郁,必须有强烈的自我觉醒意识。 我剖析了自己抑郁的原因,希望这能帮助一些有过“想死”念头的朋友。 原生家庭 原生家庭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我的性格天生是反叛而浪漫的,偏偏生在一个传统的家庭,诗意的细胞变成了“错误”,可是没有人意识到,人没办法改变性格的,就算梵高生于旧世纪的中国,他也会成为梵高的(虽然我不是梵高,我只想成为一个有诗意的人)。 父母对我制定的目标,我从未反抗过,从童年起就拼尽全力成为一个越来越不像自己的“优秀”的人。事实证明,这些“优秀”没有为我的未来产生很多作用,反倒是早期压抑在内心的“自由”最后令我得到救赎。 那些年父母不休地争吵,我不够优秀而挨的打,他们传统的思维……使我在成年之后远走高飞,并且非常坚持自己的意见。而父母却依旧习惯把成功的准则压在我的身上,看我的公众号、微博、分享的一切课程,并且告诉我该怎样做,这让我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觉得背后有双眼睛,在丈量着我的成就。这令我感觉很痛苦,也是无形的压力,常常让我失声痛哭出来。 我后来和父母讲清楚我内心的感受,他们终于不再紧盯我的生活而是选择放手,让我成为真正想成为的人,而不是一个“足够优秀”的人,我自此才松懈下来。 交际圈 我在抑郁的时候一直没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交际圈,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 我一直崇尚高度的自由,我会拒绝任何一个参与我的生活并给出自以为是的判断的人成为我的朋友。偏巧那时的朋友圈,充斥着会喋喋不休地告诉我“买房车是错误的”,“搞文艺的人活不起”,“你真不应该离开奥克兰”的人…而更有人在联系不上我的时候,扬言要报警,一条接着一条的留言,让忙碌中的我怒不可遏。 现在的交际圈是我所喜欢的,大家都是有梦想肯奋斗的人,不会每天都花时间在一起,但定期都会自发地聚在一起交流心得,没有“捆绑”,没有“评判”。 在朋友面前,你需要做个好人,做个知心的听众,做个温柔的支持者。但在梦想面前,你必须做个“坏”人,你要知道,什么是自己最想要的,哪怕它遭到所有人的反对。 我后来还知道了,遇到不想维持联系的人,换个电话号码即可,不用特意去死。 压力 我的责任感很强,早先是来自家庭的“千万别被爸妈打”的恐惧,后来形成了习惯,就是做每一件事都“不要让别人失望”。 那些自尊心太强,什么都要做到完美的人活起来是很危险的,因为总有一些事是你无法做到完美的,这极易引起情绪的全面崩盘。 我那时就是积攒了太多的工作,微信上每天都收到近千人的留言,常常令我措手不及。后来发现,如果说了“对不起,我不能做”,也不是世界末日呢。 把我治好的是新西兰的夏天,还有上次回国时闺蜜小千对我说,“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的手软软的,若不是为我多担了份忧愁,她的眼睛还是像她十四岁时那样天真。 治好我的还有一份遗嘱。 别担心,是因为一位律师朋友揶揄我的房车,“你也是有房有车的人了,突然间要是有了意外,谁是受益人啊?” 于是我真的开始认真写,结果写着写着,那些“死后希望别人要做的事”就变成了“死前我要做的事”。 我要去迪拜,去巴黎,去东京…… 我还要学自制酸奶,学做乳酪蛋糕,学做大家都爱吃的螺蛳粉…… 我要看到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在海滩上拉着女儿的手漫步…… 每个人都想过死,但很多人最终选择活下来,靠的就是这些意外发掘的期待吧。 要说还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要分享,那就是,活着比死去更考验勇气。 而那个对我提问的朋友,我想告诉你以及所有和我们承受过一样痛苦的朋友: 每一个你看似跨不过去的坎,一定有除了“死”以外的解决方式,一定有的。 帖间广告位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