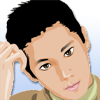 |
楼主(阅:8941526/回:0)毛翰:市歌的困境与出路
词作家:毛翰
今人所谓市歌,是指一座城市的形象歌曲,兼有宣传和广告之功。一首好的市歌,足以展示一座城市的魅力,对内可以凝聚人气,鼓舞人心,培养自豪感;对外有助于提高城市的美誉度,吸引商贾游客,招揽人才,繁荣经济。 以商业的眼光看去,推出市歌,实际上是一种以音乐文学为手段的城市品牌的营销策略。但这种营销并不容易,一首经典的市歌,可遇不可求,极为难得,而一首词曲很烂的市歌,恰恰是在昭告天下,那是一座不入流的城市,危邦不可入,烂市须绕行。
1 中国古代不大有“市歌”一说。《全唐诗》仅有一处出现“市歌”,李商隐《镜槛》诗云:“隐忍阳城笑,喧传郢市歌。”其中“阳城笑”的典故,出自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形容美女“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与之对应的“郢市歌”自然也魅力十足。但那“郢市歌”是指楚国都城(郢都)传唱的歌,并非现代意义的市歌。一直到明代,徐渭《奉师季先生书》所谓“塞曲、征吟、市歌、巷引”,其“市歌”还是泛指流行于市井的歌谣,而不是一个城市的形象歌曲。 不过,中国古代无市歌之名,却有市歌之实。类似市歌的作品,在中国其实是古已有之。中国古代最典型的市歌,莫过于北宋词人柳永那首著名的《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 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 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望海潮》这一词牌,为柳永首创,其所望应该是钱塘潮吧。写尽了杭州的繁华和诗意,写尽了其人文与自然之美,那不就是一首杭州市歌吗?作为市歌,它太出色了,甚至还让杭州这座名城以及整个江南,招致了敌国的觊觎。据说,金主完颜亮听了此歌,“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吴山之志”,第二年竟以六十万大军南下攻宋。 受了柳永(约984-1053)此歌的影响,北宋词人沈唐(约1022-约1075)也填过一首《望海潮》,其词是写给太原知府的,讴歌太原的风光形胜,怀念太原昔日的儒将才子风采,也近乎太原市歌:“山光凝翠,川容如画,名都自古并州。萧鼓沸天,弓刀似水,连营十万貔貅。金骑走长楸。少年人一一,锦带吴钩。路入榆关,雁飞汾水,正宜秋。追思昔日风流。有儒将醉吟,才子狂游。松偃旧亭,城高故国,空余舞榭歌楼。方面倚贤侯。便恐为霖雨,归去难留。好向西溪,恣携弦管宴兰舟。” 柳词是“钱塘自古繁华”,沈词是“名都自古并州”;柳词是“参差十万人家”,沈词是“连营十万貔貅”。沈词明显是对柳词的模拟和翻唱。柳永《望海潮》是杭州的千古绝唱,沈唐《望海潮》也应是并州(今太原)的古今第一颂歌。 今日杭州,何必还要去辛辛苦苦地征选什么市歌?把柳永那千古传唱的《望海潮》拿来,重新谱一个曲就是了,如果原曲失传的话。那“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不是杭州永远的梦吗?羌管醉吟晴日,菱歌夜泛西湖,长者垂钓,少女采莲……尚得如此,都市夫复何求?只要那“千骑拥高牙”的皇亲贵戚有点雅趣,“醉听箫鼓,吟赏烟霞”,不要太过骄横太过贪腐,就好了。 不过,前几年,徐州征集市歌,所有的应征歌词没有一首让主办方满意的,于是有人提议,干脆就用元代诗人萨都剌的那首《木兰花慢•彭城怀古》:“古徐州形胜,消磨尽几英雄。想铁甲重瞳,乌骓汗血,玉帐连空,楚歌八千兵散,料梦魂应不到江东。空有黄河如带,乱山回合云龙。汉家陵阙起秋风,禾黍满关中。更戏马台荒,画眉人远,燕子楼空。人生百年如寄,且开怀,一饮尽千钟。回首荒城斜日,倚栏目送飞鸿。”此议得以实施,徐州市歌问世。然而,由谷建芬作曲、韩磊演唱的这首歌,虽然安了一个《一饮尽千钟》的歌名,不乏大气,却怎么也不像是一座现代中国城市的市歌。 一连串的“消磨尽”“楚歌八千兵散”“陵阙起秋风”“戏马台荒”“百年如寄”“荒城斜日”,还有一而再再而三的“空”叹(玉帐连空、空有黄河、燕子楼空),这能激起徐州人的自豪感吗?能展示今日徐州的城市魅力吗?好一片荒城墓地,好一派破败荒凉,你让今天的中国人都去徐州凭吊历史遗迹吗?看来,市歌不能一味“怀古”,市歌还是得侧重“颂今”,不必炫耀“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总得唱唱“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给人一点阳光青春和积极向上的感觉吧。 一直到20世纪,国外才有了市歌,例如,日本的《横浜市歌》(1909),波兰的但泽市歌《为但泽》(1920)。 而20世纪上半叶的几首中国市歌,多与日本侵略有关。1920年问世的《台北市民歌》,由两位日本人分别作词作曲,日语演唱,形同台北市歌,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光复。1935年,《满洲日报》发表启事,征集《大连市歌》的歌词,随后又征集其曲。应征入选的皆为日籍作者。歌词为日语。1936年,伪满齐齐哈尔市公开征集市歌,无人响应。被强邀出来的当地才子、爱国志士胡斗南拒绝“王道乐土”“日满协和”的规定主题,借着对乡土民风的歌吟,表达齐齐哈尔人民对家国的热爱,隐含对敌寇的憎恶。试看当年这首《齐齐哈尔市歌》: 洋洋嫩水,莽莽龙沙。 唯我齐市,富庶何加。 民风朴厚,轻浮华。 讲道德,重礼让,力戒骄奢。 勤工商,习劳作,更乐桑麻。 弦歌不辍,尚文化。 梯航四集,烟火万家。 勿荒勿怠,进展无涯。 中国现代的市歌热,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热潮犹在,此起彼伏。迄今为止,征集过市歌的城市数以百计吧。上网搜索一下,已经拥有市歌的城市真不少,有的曾经由官方认定,有的只是民间在鼓吹。 试随机抄录一部分,排名不分先后:常州市歌《龙城风光》,赤峰市歌《草原上有一座美丽的城》,个旧市歌《你有两个名字》,广州市歌《广州之歌》,哈尔滨市歌《太阳岛上》,杭州市歌《梦想天堂》,淮安市歌《香溢淮安》,连云港市歌《在海一方》,大连市歌《大连之恋》,牡丹江市歌《雪城》,南京市歌《南京,我心中的城》,南通市歌《南通好家园》,沈阳市歌《沈阳啊沈阳》,石家庄市歌《飞翔石家庄》,苏州市歌《苏州好风光》,宿迁市歌《清清骆马湖》,无锡市歌《太湖美》,徐州市歌《淮海大地上》,扬州市歌《好一朵茉莉花》,阳江市歌《永远的眷恋》,镇江市歌《我家在镇江》,湘乡市歌《湘乡市市歌》,孝感市歌《孝感》,武汉市歌《武汉之歌》,日照市歌《日照海天》,唐山市歌《唐山之歌》,高雄市歌《一朵木棉一份情》,基隆市歌《美丽的基隆》,大理市歌《蝴蝶泉边》,蚌埠市歌《美丽珠城》,张家口市歌《美丽的张家口》,珠海市歌《浪漫珠海》,五指山市歌《我们都是五指山人》,枣庄市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天津市歌《天津我爱你》,吉林市歌《北国江城吉林我故乡》,林州市歌《推车歌》,绍兴市歌《水乡吟》,莱州市歌《我们是莱州人》…… 不过,今日市歌的产生,往往来自征歌,征歌的结果通常却并不乐观。要么是大张旗鼓地征歌,作品如雪片飞来,却无一能入法眼。要么是一时看走了眼,拍板定为市歌,却得不得市民的认同,渐渐被时间遗忘。而词美曲美,让本市居民感觉与有荣焉,乐于传唱,并不胫而走,风靡天下,这样的市歌则如凤毛麟角,难得一见。 1989年1月,广州市政府通过报刊高调征集市徽、市歌。次年3月21日公布市徽、市歌评审结果,市歌《广州之歌》问世,其词云: 高高云山滔滔珠江,历史名城革命故乡。 鲜艳的红棉迎春开放,灿烂的阳光普照五羊。 社会主义道路无限宽广,向着明天向着前方。 广州广州,英雄的城市,美丽的家乡。 稻穗鲜花献人民,你为祖国添芬芳。 广州广州,英雄的城市,美丽的家乡。 团结友爱求实进取,你为中华闪耀光芒。 八年后,1998年3月广州市政府下发通知,说是由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禁止自行制作和使用地方旗、徽的通知》,广州市决定不再制作和使用市徽,《广州之歌》亦不再作为广州市市歌。可是,中办、国办禁止的是地方自制的旗、徽,并没有禁歌,《广州之歌》不再作为广州市歌,应该另有原因吧。什么原因呢?大概跟歌词本身的思想和艺术水平有关,跟时代的审美趣味的嬗变有关。 1992年4月1日(愚人节),武汉市向全国公开征集市歌。一首《武汉之歌》,据说经过层层选拔,从千余参选作品中脱颖而出。1994年9月23日,武汉市第九届十次人大会议通过决议,定之为武汉市市歌。其词云: 晨钟催醒巍巍江城 东方朝日正在升腾 长江汉水春潮滚滚 扬起新的时代精神 让莽莽龟蛇铭记 让白云黄鹤作证 用我们的热血铸造起荆楚之魂 让莽莽龟蛇铭记 让白云黄鹤作证 用我们的脊梁托起一个新的乾坤 然而,近二十年后,武汉市“两会”召开,有委员指出,武汉的“市歌”几乎没有人会唱,而武汉太需要一首市歌来提升城市的内涵和文化特质。有委员表示,在提出“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武汉精神后,需要重新审视当年市歌歌词,可以重新谱写,并加大传唱推广力度。其实,重新谱写,大力推广,也未必就能奏效。 这种征歌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倒是征歌成功的例子鲜有所闻,我们至今都不大听说哪个城市通过征歌,征来了一首风行全国的经典市歌。特约著名词曲作家为之创作,好像也没有什么成功的先例。而适合做市歌的作品往往都得之于无心插柳。于是,一些城市转变思路,不再辛辛苦苦地去征词征曲,而是把目光转向现有的流行歌曲,试图从中选出一首,作为自己的市歌。 2002年底,无锡市就抢先宣布《太湖美》为自己的市歌。照理说,太湖周围东南西北四座城市,苏州、湖州、宜兴、无锡,最有理由用《太湖美》作市歌的,应该是湖州,因为人家是湖之州,名正言顺呀。无锡本来有自己的歌《无锡景》:“小小无锡景呀,盘古到如今,东南西北共有四城门呀,一到(仔)民国初年份呀,新造(那)一座(末),光(呀)光复门呀。”传唱于抗战以前,无奈其内容有点陈旧。另有《小小无锡景》“风景虽好人辛酸,琴妹卖唱诉衷肠”,又过于伤感。 2003年3月22日,扬州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宣布将今天已经享誉世界的《茉莉花》定为自己的市歌。这更不免有掠美之嫌,《茉莉花》流播四方,誉满中外,岂止为扬州所专有。《茉莉花》作为民歌,据说起源于五台山佛乐《八段锦》,随着僧人云游传到江南,形成诸多不同版本,1940年代被搜集加工的那个版本并非出自扬州,而出自南京六合。扬州市因而底气不足,其决议说,其它城市如果要用《茉莉花》做市歌也可以,虽欲化公为私,却不敢独家垄断。 如果可以这样抢注,上海倒是不妨把《歌声与微笑》拿来做自己的市歌。“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让客人带回家的是歌,也是产品,是物质和精神的文明,让客人留下的则是对于上海的满意的笑容,到明天,一切还会变得更加美好。作为东方大都会,上海面对全中国以及全世界,应该有这份自信和承诺。《歌声与微笑》是1986年第一届上海电视节的会歌,上海也可以算做其原产地,尽管词曲作者王健、谷建芬都在北京。 然而,无锡用《太湖美》做市歌,扬州用《茉莉花》做市歌,上海用《歌声与微笑》做市歌,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推出市歌的目的,是为了宣传自己的城市,而《太湖美》根本就没有提到无锡,《茉莉花》根本就没有提到扬州,《歌声与微笑》根本就没有提到上海。市与歌无缘,何必拉郎配?但见泪痕湿,不知歌颂谁? 市歌难以征选,其实不足为怪。20世纪上半叶,中国屡次征选国歌,也颇为不顺。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2月,教育部发布征集国歌的公告。2月25日第22号的《临时政府公报》,刊登出一首国歌拟稿《亚东开化中华早》:“亚东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河山普照。喜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 7月10日,教育总长蔡元培在北京召集会议决定,再度公开征求国歌歌词,得稿300余篇,仍然选不出理想之作。教育部于1913年2月26日致函海内名家蔡元培、王闿运、张謇、严复、梁启超、章炳麟、马良、辜汤生、钱恂、江荣宝、沈曾植、沈曾桐、陈三立、樊增祥、吴士鉴等十五人,特约为国歌作词。仅章炳麟、张謇和钱恂交卷,三人之作亦未获通过。其中章炳麟词云:“高高上苍,华岳挺中央,夏水千里,南流下汉阳。四千年文物,化被蛮荒,荡除帝制从民望。兵不血刃,楼船不震,青烟不扬,以复我土宇版章。吾知作乐,乐有法常。休矣五族,无有此界尔疆。万寿千岁,与天地久长。” 倒是汪荣宝以上古《卿云歌》做国歌歌词的建议,得以采纳。《卿云歌》曰:“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汪荣宝认为其“气象高泽,超越万流,而卿云兼象国旗,光华隐寓国号,播诸弦管,尤足动人爱国之思。且帝舜始于侧陋,终以揖让,为平民政治之极则……”鉴于歌词过于简短,建议末尾加一句“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据说那是舜当年唱完《卿云歌》的感叹之词,载《尚书大传•虞夏传》。不过,此后《卿云歌》终因其词古奥,其歌并未流行。其后,又经历了袁氏当国暗寓其称帝野心的《中国雄立宇宙间》和《国民党党歌》代国歌等。 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向全国公开征求国歌,收到歌词694首,也无一可用。开国大典在即,只得以《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尽管“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的词句并不恰切,“居安思危”的解释也有点勉强。 而被否定了的众多歌词,不乏出自名家之手的,包括郭沫若的8月间创作一首《新华颂》:“人民中国,屹立亚东。光芒万丈,辐射寰空。艰难缔造庆成功,五星红旗遍地红。生者众,物产丰,工农长作主人翁。使我光荣祖国,稳步走向大同。”(第二、三段略) 有趣的是,就在第二年,1950年9月,一位来自天津的名不见经传的青年王莘,独自走在天安门广场,红旗、鲜花让他顿生豪情,连词带曲,心底竟涌出一支磅礴大气的《歌唱祖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应该说,这才有点国歌的气象。如果它在一年多以前诞生,拿去应征,国歌可能就非它莫属了(当然,也可能被埋没,当初《天津日报》就曾退稿)。 4 抢注一首全国流行的歌,单方面宣布为自己所有,这搞法有点可笑,也不大合法。但如果一首歌,本来就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理应属于某地,某地宣称它为自己的歌,那就没有多少好争议的了。剩下的,只是那首歌的水平如何,是否具有经典性,是否足以让你那个地方那座城市平添魅力?说白了,那首歌是否具有“营销价值”? 如果四川的康定要用《康定情歌》做自己的市歌,湖北的洪湖要用《洪湖水,浪打浪》做市歌,大理要用《蝴蝶泉边》做市歌,香港要用《东方之珠》做市歌,拉萨要用《回到拉萨》做市歌,海南岛上的三亚要用《请到天涯海角来》做市歌,都没有什么好争议的,那首歌,唱的就是那个地方,合该做人家的形象之歌。 不过,时过境迁,如果上海要用《夜上海》做市歌,那座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不夜城里,酣歌醉舞者内心的伤悲和无奈,如今是否依旧,就值得推敲了。如果山东临沂要把《沂蒙山小调》原封不动地拿来做市歌,枣庄要拿一首老电影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做市歌,湖北的洪湖要用《洪湖水,浪打浪》不加剪裁地来做市歌,年轻的市民是否接受,也是不能不考虑的。 如今,多数城市的市歌不合格,达不到对内提神、对外广告的目的。 或许,市歌还是要等它自己长出来,不能强行拔出来。强行拔出来的东西,往往是缺乏生命力的。市歌的甄选应该宁缺不滥,不可降格以求。 然而,守株待兔,让一座城市坐等一首经典的市歌,从天上掉下来,从地下冒出来,那可能几百年都等不到,盼歌心切的城市,不可能有这份定力。于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去做百分之百的努力,悬赏重金去征集,或特约名家去创作,仍然是必要的。 市歌的创作和甄选如何走出困境,最重要的一条出路,应该是改变市歌的创作和甄选的标准。 由于市歌是城市的形象歌曲、宣传歌曲,旨在宣传自己这座城市的美好宜居,品质非凡,商机无限,前程无量,市歌的歌词,无非是夸耀自己这座城市的好山好水、风情风物、文化积累、现实成就、发展前景,以及所谓城市精神,这就使得其歌词创作,很容易形成一种套路,一种标准的套话。 通常,一首市歌的歌词,如果找不到一个别致的构思,就只能去东拼西凑,看看这座城市有一座什么山,有一条什么河,有什么名胜古迹,物产风情,风水祥瑞,出了一些什么名人轶事、历史事件……把所有值得夸耀的东西拿出来夸耀一遍,再把未来的愿景,甚至现任官员的政绩,都拿出来夸张地展示一番,就堆砌成篇了。 于是,市歌歌词往往成为最没有艺术魅力、最索然无味的八股文字,成为最让作曲家头疼、歌唱家叫苦的东西,最不受听众欢迎,最不会流传的东西。 鉴于今日市歌屡屡失败的教训,关于市歌的创作和甄选,人们想当然的、相沿成习的那一套标准,其实是大可质疑的。 就艺术魅力和宣传效果而言,中国现代最成功的市歌,也许莫过于《康定情歌》吧。如果没有《康定情歌》的广为流传,今日中国和世界,有几个人知道川西高原上还有个康定?有几个人会想到去康定那座溜溜的城旅游寻梦呢? 而《康定情歌》原本只是一首情歌,它根本就没想过成为市歌,成为康定的旅游宣传之歌,它只是在唱着一个发生在康定小城的爱情故事。 如果有人告诉我们一段秘史,说《康定情歌》原本就是一首市歌(康定曾经是西康省的省会),是康定地方当局精心策划的一首关于康定的宣传歌曲、广告歌曲,那它也太狡黠了,太鬼了,它完全掩藏了自己的宣传、广告动机,瞒过了天下所有的歌者和听众,它完全不曾抒写康定的风光名胜、人文历史,以及所谓城市精神,它只是歌名冠以“康定”,还有一句“康定溜溜的城”。至此,人们应该恍然大悟:市歌原来竟还有这样一种作法!一首歌只要点出了某个地名,它就具备了宣传、广告的功能和性质,就成了某个地方的宣传、广告之歌。 让我们重温《康定情歌》,看看它是怎么写的,看看它是怎么瞒天过海,借情歌之名,行广告之实的吧: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 端端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 月亮弯弯,康定溜溜的城哟 李家溜溜的大姊,人才溜溜的好哟 张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她哟 月亮弯弯,看上溜溜的她哟 一来溜溜的看上,人才溜溜的好哟 二来溜溜的看上,会当溜溜的家哟 月亮弯弯,会当溜溜的家哟 世间溜溜的女子,任你溜溜的爱哟 世间溜溜的男子,任你溜溜的求哟 月亮弯弯,任你溜溜的爱哟 如果康定不曾有过这样一首情歌,如果今日康定公告天下,想要征集一首康定市歌,而有词作家作了这样一首歌词,康定会采用吗?会不会说离题万里,风马牛不相及呢? 《康定情歌》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地方特色可言,“跑马山上一朵云,端端照在康定城”,“李家大姊人才好,张家大哥看上她”,这景色,这故事,可以发生在康定,也可以发生在康定之外的别的许多地方。只要把歌中的“康定”二字删去,换成别的地名,譬如与康定相邻的“泸定”、“丹巴”、“雅安”,这首歌就不再是康定情歌,而是“泸定情歌”“丹巴情歌”“雅安情歌”了。 常常有人提醒我们,写市歌,要注意表现城市精神。可是,是否每一座城市真的都有一种只属于自己、有别于他人的城市精神?“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真的就是武汉独有的城市精神吗?请问,中国有哪一座城市不想“敢为人先,追求卓越”,哪一座城市“甘落人后,甘于平庸”?就算有的地方的人热衷“打拼”“创业”,有的地方的人惯于“慢节奏”“休闲”,人生姿态大致也只有这两种,决不至于全国几十座大城市,几百座中等城市,几千座县城,都各有自己的独具个性的城市精神吧。 极而言之,一首市歌,只要提到那座城市的名字就够了,例如《康定情歌》。或者,只要写了那座城市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景点也就够了,例如哈尔滨市的《太阳岛上》。或者,只要写出其某一有代表性的物产也就够了,例如景德镇市的《景德镇瓷器》。 在市歌构思雷同、有如八股的今天,至少应该允许一部分市歌,它们偏偏不像市歌,不太像市歌,或太不像市歌。 其实,一首歌究竟像不像市歌?拉开时空距离,超然一点看,那结论可能恰恰相反:像而不像,不像而像。不像反而大像,太像反而不像。 除此以外,市歌的遴选还应强调什么原则,也许莫过于要求负责选歌的官员,不可怀有私心,不要乘机推出自己的劣质之作。须知,选歌和选美一样,是难以徇私舞弊的,选美所选出的美人,要经过无数眼睛的挑剔,选歌所选出的市歌,要经受无数耳朵的监听。如果不想被万人唾骂,还是有点自知之明为好。 中国最好的市歌,都出自优秀诗人的手笔,或出自民歌。中国古代最优异的市歌《望海潮》,恰恰是没有做官的柳永所写。可叹今日,官壮怂人胆,赢家更通吃,一个人只要官做大了,便连诗也敢写了,词也敢填了,字也敢题了,鸦也敢涂了,眼也敢现了,人也敢丢了。 5 江山也要文人捧,城市也须歌儿唱。今日中国的市歌,大概可分三类:一是经典之作,例如《康定情歌》,足以让一座城市平添异彩,名播天下。二是平庸之作,勉强及格,凑合着也能听,今日市歌大多属于这一档次。三是拙劣之作,其来路蹊跷,词不成词,调不成调,难听刺耳,自取其辱。 我们的家,住在天堂, 碧绿的湖水荡漾着美丽的梦想。 我们的家,住在天堂, 美丽的梦想期盼明珠耀眼在东方。 你把你的名字写在云的脸上, 让所有的远方看见你的模样。 你把你的春天挂满每一个脸庞, 让远来的翅膀不想家。 你把你的曾经刻在日月的中央, 让成长的天使懂得洁白的主张。 你把你的未来放在我们的肩上, 让友爱的心门不再关上。 城市里的每一棵树,它们都知道 每一片绿色是你的阳光。 城市里的每一条路,它们都知道 有了爱,理想不再是希望。 ——杭州市歌《梦想天堂》 杭州从1996年开始征集市歌,至2002年《梦想天堂》问世,据说已被正式定为市歌。读其词,听其歌,感觉不是很差。但“天堂”这个语象,来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古谚,苏州在前,杭州在后,杭州人如此自夸,一点也不心虚吗?还有,“天堂”是天上的国度,是人死之后灵魂归宿的地方,“我们的家,住在天堂”,多少有点瘆人。还有,最后一句“理想不再是希望”也不大通。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有宋人柳永的经典名篇《望海潮》在前,今人写市歌,还是心存一点敬畏吧! 太阳祝福你,春风祝福你, 高山祝福你,大江祝福你。 两百六十万父老乡亲, 捧出一颗颗赤诚火热的心。 向你海内外,血脉相连的弟兄, 致以深深地祝福表达殷殷之情。 啊黄石我的家乡多么美丽, 啊黄石我们深深祝福你。 祝福孩子们生机勃勃, 象一朵朵鲜花美丽动人。 祝福年轻人雄鹰展翅, 追求理想四海洒豪情。 祝福中壮年跨上骏马, 人生能有几次搏,爱拼才会赢。 祝福老年人红霞漫天, 寿比南山不老松,永远年轻。 …… ——黄石市歌《祝福黄石》 这首《祝福黄石》,号称黄石市歌,由黄石市委书记亲自作词,原词的篇幅两倍于此,外加一个结束句。听罢此歌,我辈感慨莫名。书记市长们公务繁忙,日理万机,连讲话稿都有秘书代拟,为市歌作词作曲这种卑贱的手艺活儿,就不劳您亲力亲为了吧。您老人家如有雅兴,可以匿名参赛,为别的城市写一首歌。您自个治下的这壹亩三分地,就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让群众去捣鼓吧。 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在。 海南岛上春风暖,好花叫你喜心怀。 三月来了花正红,五月来了花正开。 八月来了花正香,十月来了花不败。 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花果遍地栽。 百种水果百样甜,随你甜到千里外。 柑桔红了叫人乐,芒果黄了叫人爱。 芭蕉熟了任你摘,菠萝大了任你采。 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 来呀来呀,来呀来。 ——三亚市歌《请到天涯海角来》 《请到天涯海角来》的歌词是郑南先生的杰作,作于1982年,想必最初只是有感而发,并没有想写什么市歌,结果竟大获成功,后被海南三亚奉为市歌。其词两段,先写花,再写果,构思自然天工,隐含一点美色的诱惑和挑逗。许多人就是听了这首歌才动心去海南旅游的。而他刻意创作的《广州之歌》,其广州市歌的尊号却得而复失。按照流行的市歌标准去衡量,《广州之歌》其实很规范,很像是一首市歌,《请到天涯海角来》则不合规范,完全不像市歌。然而,规范的广州市歌只存活了八年,不合规范的三亚市歌却生机盎然。 当然,一首歌拯救不了一座城市,当海南旅游失序,三亚商家肆意宰客,事件曝光,全国哗然,有一首《请到天涯海角来》(宰客版)应运而生,就令人哭笑不得了:“刚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司机把路带。推荐餐馆吃海鲜,谁料进去就认栽。邻座哥们刚问价,捞出活鱼地上摔。上秤高喊十一斤,噼里啪啦六千块。来呀来呀来呀,宰呀宰呀宰呀,来呀来呀,宰呀宰。……” 鼓浪屿白鹭飞翔,浪漫写在天上。 鼓浪屿鼓动青春来,青春啊一路歌唱。 日光岩上眺望,长虹飞跨海浪。 天有情,海有爱,我们拥有你美丽的厦门港。 母亲城碧波荡漾,海岸几度沧桑。 母亲城广厦千万间,凤凰花门前开放。 皓月园中徜徉,两岸华灯初上。 天有情,海有爱,我们拥有你美丽的厦门港。 鼓浪屿琴声悠扬,日夜在海天回荡。 有多少人间失落的梦,都在这里珍藏。 珍藏点点星光,珍藏鸟语花香。 天有情,海有爱,我们拥抱你美丽的厦门港。 《鼓浪屿之波》诞生于1981年底。其题旨是宣传“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这一新的对台方略。随着两岸三通的实现,台胞想从厦门回台湾已经相当便捷,渴望见到基隆港,买一张机票或船票,见去就是了,再也用不着“登上日光岩眺望”了。所以,此后再唱此歌,就不免显得矫情。但这首歌的旋律太美了,在厦门深入人心,已经成为厦门人心中的厦门之歌。2007年厦门两会上,就有提案建议将《鼓浪屿之波》定为厦门市歌,由于其歌词与厦门市歌文不对题,提案被否决了。是呀,“我渴望,我渴望,快快见到你美丽的基隆港”,人家极力背你而去,在厦门一刻也不愿多留,一点也没有“此间乐,不思台”的缠绵,这让厦门情何以堪?于是,沿用《鼓浪屿之波》的旋律,改变其主题,重新填词,成为许多厦门人的共识。于是,有好事者为之重填了上面这首词。厦门、福建有文化名流如郑小瑛、孙绍振,对新词极为赞赏。也有人不以为然,力主另起炉灶,重新征词征曲,坚信天上会掉下第二个林妹妹。 (原载《词刊》2016年第9期) 帖间广告位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