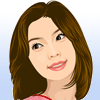 |
楼主(阅:63953255/回:0)权力还在太后手里,但国运不在【上】
1901年1月29日,尚在西安“西狩”(逃亡)的大清朝廷发布上谕,以一番痛彻心扉的言辞,宣布即将开始新政。历经庚子年的天翻地覆,自幼长于深宫的皇帝沉痛于国家沦陷,将其归因于根深蒂固的弊病:“深念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当此危急存亡之际,他迫切地需要帝国的高级官员们献言献策各抒己见。 这道以光绪帝名义发出的上谕,是一份非常有趣的文献,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戊戌年所发生的事做了一份“总结陈词”。 1898年逃亡海外的康有为,被称之为“康逆”,他“藉保皇保种之奸谋”,“为离间宫廷之计”,引诱追随者谋逆,他所讲的新法根本不是变法,而是乱法。上谕里还委婉透露当年围园之谋的存在,“该逆等乘朕躬不豫,潜谋不轨”,于是,才有了皇帝恳请皇太后训政,剪除叛逆。 接着,上谕所言则颇有辩白的意味:“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也就是说,太后并非顽固守旧,而皇帝也不是老臣们的敌人。接下来的几句则更加意味深长:“酌中以御,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见。今者恭承慈命,壹意振兴,严怯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这表示太后和皇上,在革故鼎新上达成了共识,要同心协力让国家转弱为强。 从戊戌变法后,皇帝和太后的关系极为微妙,且催生出庚子之变,血色激荡,太后拖着皇帝仓皇西狩;如今则以“母子一心”为标榜。也难怪大臣们心存疑虑,不敢信以为真。菜市口的鲜血尚殷,如今流亡在外的朝廷宣布变法,一向知权达变的帝国高级官员,自然担心太后此举是“引蛇出洞”,于是,在上谕规定的两个月内,竟然没有一个大臣复奏,提出新政具体举措。 此后,诏书一道接着一道。四个多月后,6月3日,光绪帝再次发布上谕,开宗明义点出“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要求各部官员和地方督抚学政,保荐人才,“朝廷振兴百度,母子一心,惩往日之因循,思得贤以辅治”。10月2日,朝廷再次发布上谕,督促各省支持变法、切实开展新政工作。这道上谕亦是奉皇太后懿旨,第三次提到要“母子一心,力图兴复”。 此后,在两宫从西安回銮途中,慈禧太后发布谕旨,废去1899年所立的“大阿哥”。彼时慈禧太后藉光绪帝病重,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入继同治帝为嗣。 得知这一消息,湖广总督张之洞当日便致电自己的姐夫、军机大臣鹿传霖:“闻已有旨废储,钦颂。此母子一心之实据也。”虽然太后谕旨中说将来还要选择一位继承人,大臣们仍在困惑之中,但毕竟这是太后释放出的善意。或者可以说,太后要在回到北京之前,在天下人,尤其是西方列强面前,塑造一个母子一心致力于新政的形象,以对抗革命势力和缓解外部压力。事实上,在看到新政的上谕后,盛宣怀就说:“今两宫一心,已饬议行新政,将来中外必能益加修睦,悉释前嫌。”其着眼点亦在于改善国际形象,争取列强支持。 不到三年时光,从以雷霆之势绞杀维新,到全面维新,在某些方面甚至更为激进,可以说是军事惨败紧接着巨额赔款丧权辱国后的连锁反应,当政者所得的残酷教训可谓空前。三年前被后人划归于不同阵营的 “新派”或“旧派”,可能都不会料到有此一番翻覆。 数次标榜“母子一心”,正见得从前有不一心处。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关系,是晚清最令人困惑也最迷人的话题。 1875年,当18岁的同治皇帝龙驭上宾后,慈禧太后没有按照惯例选择一位低一辈份的近支皇族承继大统,而是将她的小叔子醇亲王奕譞和亲妹妹的儿子载湉作为嗣皇帝。据《翁同龢日记》载,宣诏当日,奕譞“惟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有皇位要继承却吓晕过去,现代人大概很难理解这样一种祸福不由自主的恐惧心态。这样的历史细节,恰好展现出珠帘背后的积威,有何等沉重的震慑力。 在1898戊戌年,这种震慑力更展露得淋漓尽致。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发“明定国是”诏书,维新变法揭幕。仅仅四天之后,草拟这道诏书的翁同龢就被开缺回籍。密切关注变法进程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预言了几个月后的政变:“虽然闪电已经击倒了一位大人物翁同龢。翁氏和李鸿章是对头。现在看来,翁氏的忙乱、守旧或许助长了一场宫廷政变,使大权落到慈禧太后手里,于是皇帝对他颁下无情的谕旨。据说22日还会有事,可能是那位老太太发现,她尝到的血,不致引起祸害,因而会去追求更大的牺牲品。” 历史学家茅海建详细考证过戊戌变法的过程与原委,精确还原了每一天的重要场景。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是,在9月中开始,出现权力异动,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在缩小,慈禧太后权力在扩大,直至走向前台,而在这一段危机四伏的政潮下,戏迷慈禧太后照旧看戏不辍,显示出这位铁腕人物对把控力的绝大自信。 9月18日(农历八月初三)是戊戌年最为关键的一天。这天,光绪帝离开颐和园回宫,他早晨六点在寝宫进行早朝,然后到乐寿堂向太后请安、侍早膳,上午十点多开始陪同看戏。光绪在下午两点离开了颐和园,慈禧太后则一直让戏演到了晚上。当晚,慈禧太后决定第二天离开颐和园回西苑。也是在这个晚上,谭嗣同夜访法华寺,试图说服袁世凯参与围园之谋。 茅海建先生认为是一道奏折让慈禧太后决定第二天回宫。御史杨崇伊请太后立即训政的这个奏折,让太后决心停止这场变法。政变发生几天后,赫德自北戴河匆匆回到北京,他告诉金登干:“此间的形势一瞬间发生了变化,我们如坠五里雾中,慈禧太后把皇帝推入阴影中,自己亲政(应该是训政)……有谣传说,皇帝很推崇伊藤博文,这与慈禧太后发动突然袭击有很大关系。”而杨崇伊的奏折里也提到了关于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传言:“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依藤果用,则祖宗所传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此前,光绪帝罢免六部官员,任命军机四章京,已经激起官僚体系的一致怨恨,而康有为策动开懋勤殿议政打破原有权力格局的目标,也造成了官员们的恐慌。于是在9月20日伊藤博文觐见的外事活动结束之后,次日,慈禧宣布训政,并下令逮捕康有为兄弟。不过,历史学家马忠文则认为,训政本身即是太后亲信庆王奕劻和在天津的荣禄密谋促成,以此来终止新政,慈禧太后至始至终都知情。 究竟慈禧是一开始观望发觉新政失控而果断出手,还是一步步剪除羽翼请君入瓮?我倾向于前者。太后一直深信光绪是自己手中的风筝,飞得再远也在控制之中。也是为了保持这种绝对的控制力,她对于任何能够影响光绪帝的人,都怀抱高度的警戒心。可以每天和皇帝接触的帝师翁同龢,戊戌年间“启沃圣心”的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都成为太后嫉恨的对象,杨崇伊奏折里所言伊藤博文事肯定也触动了太后的这根心弦。 也因此,“围园之谋”暴露出,对慈禧太后应该是极严重的心理打击。据荣禄的幕僚陈蘷龙记述:“当戊戌政变后,宫闱之内,母子之间,盖有难言之隐矣。而一班熏心富贵之徒,致有非常举动之议。东朝惑之,嘱荣文忠公从速办理……”(陈蘷龙:《梦蕉亭杂记》),东朝即指慈禧太后,她确有废掉光绪的心思。 其实,在政变后一个月,赫德就提到这种废立传闻:“有六个年轻人正在宫中接受考察,据说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在月底之前将成为皇帝……各国使馆都在寻求良方,站在皇帝这一边,出面干预,并能获得成功。但是,不是留下他,就是留下她,而她是两个人中的绝对强者,他留下的可能性的确很小。”按照陈蘷龙的说法,是因为李鸿章警告荣禄,废皇帝必然会引发外国公使抗议和各省官员声讨,甚至招致战争,荣禄将这番话转奏,慈禧这才暂缓废帝,尔后以立大阿哥作为前奏、过渡。
帖间广告位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