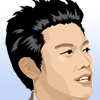 |
楼主(阅:9642872/回:0)母亲的固执,不合时宜?
【福建梯田风光】
母亲身体一向粗壮健朗,从年轻到七八十岁,一直维持强健体力,超乎一般农家妇女,因此农事再怎么繁重,总能胜任承担,一季又一季从不怠懈。 母亲的意志力更是坚强,面对父亲车祸骤然去世,庞大债务的逼迫,又需独自筹措我和弟、妹四人的学费,住宿在外的生活费,还是撑持过去,留住田产,未被打垮。 回想母亲一辈子,过得最艰辛、最苦痛,却没有能力去改变的事,除了父亲英年过世,莫过于时代变异中科技文明的冲击,直接说来就是对“文明产物”的抗拒。 1970年,我从学校毕业,选择返乡教书、定居,女友也支持,从宜兰请调来吾乡中学任教,我们一起协助母亲耕作,逐年偿还债务。 乡亲都说我很孝顺,只有我自己明白,我是何其不孝。 日常生活中,我和妻确实几乎事事依顺母亲,唯独不能接受母亲抗拒文明产品,每一样改变,都必须花费不少力气说服、要求、争取,甚至引发激烈冲突。 在所有冲突过程中,亲友眼中,我和妻是无辜的“被压迫者”,当然都支持我们,一起责备母亲落伍、老古板,跟不上时代,常拿来当作带有嘲弄意味的笑谈、趣谈,包括远在美国的大哥,偶尔回来,也大力声援,开导母亲,我们更有充足理由和后盾,理直气壮反压迫。 然而母亲终其一生抗拒文明产品,果真毫无道理吗? 从我家到任教学校,约四公里路程,既无火车也无公交车,连客运都没有。任教之初,首先要决定交通工具。 当时摩托车已入侵乡间,逐渐流行,但因父亲在我专一那年,刚买摩托车只骑了几个月便在下班途中车祸丧生,所以摩托车是母亲的梦魇,不可能允准。我能理解母亲的心情,不敢违逆。 父亲留下来的脚踏车还很好骑,我和妻在学生时代共骑的那一辆“来礼”,婚后也当嫁妆寄送过来。这两辆脚踏车骑起来备感温馨。 有几位年轻同事,骑最流线型、最拉风的“伟士牌”摩托车,有时和他们一起并行,他们尽量放慢车速,我则拼命加紧踩踏板,踩得气喘吁吁,那种景象,很值得玩味。 认真想想,多数同事从家里到学校,不过几公里路程,何况还年轻力壮,非骑摩托车不可吗? 然而时代潮流滚滚推进,有多少人挡得住,不被潮流推着走,而成为潮流的推动者? 80年代后,“轿车”逐渐普及,砍树铺水泥盖车棚的风气,快速流行,学校、机关纷纷起而效尤。母亲挡得了一时也挡不了多久,等到我的子女在村庄小学毕业,上了中学,妻为了接送小孩,母亲终究还是得接受汽车时代的来临。 70年代的农村家庭,民生设备普遍还很简陋,妻较早接受文明洗礼,所以来到农村,样样很不适应。 所有民生用水,要去屋侧古井一桶一桶汲取;浴室也要靠提水;厕所还是茅坑,每隔一段时日要定期勺起来,一桶一桶挑去田里施肥;每间卧室放置一个尿桶…… 容器大都是一片一片木片围匝起来的木桶,桶子装清水就叫作水桶,装尿就叫作尿桶,装屎就叫作屎桶,装饭就叫作饭桶,装什么就叫作什么桶,不能混用。 每一个桶子都很珍惜,不轻易弃置,围匝木片松脱、散掉,有专门“匝桶”师傅下乡来修理。 “文明”沿着电线杆一一快速侵入农村,我们赶着追随潮流,母亲则拼尽力气抗拒。 最早是冰箱。 我们结婚才一两个月,法院来查封我们家的所有财产,冰箱是妻少数嫁妆之一,也被贴上封条,母亲说好呀贴上去没关系,反正也无用。妻当然很伤心。母亲的理由:自早以来,食物处理后,用菜篮吊起来防老鼠就可以了,哪需要冰箱整天插电,“多了电费”。 从古井改变为自来水,母亲说古井水那么方便,为什么还要花钱买水?源头不知哪里来,有一天停水怎么办?又有不明气味,哪有自家古井可靠又清甜,不必怕经常要断水,夏天又清凉。 从茅坑改变为抽水马桶,母亲很难接受粪肥被冲掉,“真无彩”(真可惜),连尿也不能留下来浇菜,还要每撒一次尿,就冲一次水,多浪费。 从扇子改变为电风再到冷气机,母亲深深感慨,吹冷气哪有在树下吹风凉快?真想不通为什么宁愿把树砍掉,大家躲在房间内吹冷气。 要买电视,母亲说做戏呆、看戏憨,闲人才有时间看,我们种田人哪有那种美国时间;每天中午,店仔头电视机前,挤了一堆邻居,看得嘴仔开开,不知要下田;晚上一大堆囝仔,守在那里,不知去读书。 我在1982年出版的散文集《农妇》中,有多篇叙述这些事件,只是当年我是以幽默略带调侃的语气,当作趣事。 其实,每一次改变我们都是多么理直气壮要求母亲同意,想尽办法说服,近乎逼迫母亲顺应新时代潮流。在说服的过程中,经常发生大大小小的争执,乃至激烈冲突。 历经时日最长、争执最多、冲突最激烈的一次,大概是厨房的改变。 妻嫁过来时,我们家厨房还是使用大灶,主要燃料是稻草。大灶前墙角边堆放一小捆一小捆稻草,俗称“草”,从灶坑塞进去燃烧。 每一期稻子收割后,要将稻草扎成一捆一捆,从田里载运回家,在家屋周围空旷处,一层一层叠起来,堆成圆锥形,俗称“草墩”。 大灶前的“草”将用光时,必须花费至少一两个小时,坐在“草墩”边,抽取一小卷一小卷稻草,头尾折到中间,扎成“草”,搬进灶前放置。 以稻草为燃料,就有大量灰烬,俗称“火麸”(稻草灰),灶坑内的“火麸”每天至少要清理一次,每次都有一大畚箕。 “火麸”收集成堆,是农村很重要的堆肥;“火麸”的过滤水很润滑,是母亲的最佳“洗发精”,一向很珍惜。 然而“草”的消耗量十分快速,三五天,至多一两个星期,就需要补充一次,尤其稻草密布稻芒,接触皮肤很容易刺痒,特别是对都会人,确实是不小的家事负担。 妻极力争取要废除大灶、改换瓦斯炉,爆发多次争吵,包括姐姐、妹妹等亲友,也来“赞声”,大家联成一气指责母亲固执,跟不上时代。 母亲又委屈又生气:懒惰就是懒惰,讲那么多理由,我使用这个大灶几十年,养大你们,哪一餐让你们饿过、没饭吃?自己田里的稻草“便便”不用,要花钱去买一桶一桶瓦斯。 在亲友的“舆论压力”下,就像其他民生设备,母亲只好让步,在室外用砖块砌一个小灶,逢年过节做甜糕、菜头糕、炊肉粽,以及烧热水等耗时较久的炊事,可以派上用场。 母亲使用大灶数十年,养大我们,确实想不起有哪一餐耽误过我们,让我们没饭吃,包括每天早餐,必须带中午便当就煮饭,不然就煮稀饭。 而今家家户户都有瓦斯炉、微波炉、烤箱……设备多齐全多便利呀,然而多少家庭几乎不做早餐。或说现代人工作忙碌,但母亲的农事和家事不够忙、不够繁重吗? 母亲常说我们农村家庭,有自己的条件,何必一直要学都市人? 自从使用瓦斯炉,每期稻子收割后,田里的稻草废弃不用,只好就地焚烧,大好的资源平白浪费,又造成浓烟四起。 其实稻草功用大矣!不仅能当作大灶燃料、有机堆肥,还可编草绳、草席(或坐垫)…… 其实以往许许多多的民生用品,都取自农作物,我一直相信,如果以往用心“研发”,一定可以制作得更精良,可以推广得更流行;而且取之于大自然,还之于大自然,不会造成地球负担,环境污染。很可惜在工业产品冲击下,一项一项快速被取代而消失。 1999年9月母亲过世后,年复一年,对母亲的思念越来越深,最常出现在我脑海中的,便是和母亲为了科技文明而争执、冲突的画面;每一个画面,都如针刺在我的内心,隐隐作痛。 母亲晚年经常无限感慨地说:会坏!会坏!时代只有越来越坏!不会越好。 有些邻居劝母亲:你自己不要坏就好,不必操烦那么多。 我越来越理解,母亲一辈子抗拒文明产品,考虑的除了金钱的浪费,必然还有更深沉的隐忧、不安。 母亲不识字当然不懂得什么资本主义,不懂得消费刺激生产,生产带动经济,同时也制造污染。她只明确知道,人的生活不该也不必那么浪费。 例如两位妹妹的鞋子。 1980年我曾在一篇《了尾仔》的小文章中有一段描述: “自从两位妹妹从学校毕业,踏入社会工作以后,不断接受都市文明的陶冶,家里各式各样的鞋子,也就多起来了,每次妹妹回家,为了所穿的鞋子,尖头的、高跟的、花花绿绿的……总要引母亲一顿生气: 有平底布鞋可以穿,又省钱又轻便,已经很好了,偏偏要穿那些“阿里不打”的三八鞋,连走路都走不稳,就是太闲了,才有这些花样。” 春节前几天,照往例家家户户都要清洁大扫除,妻搜出了好多双旧鞋,准备丢掉,被粗手大脚,日日和泥土为伴,经年少有几天机会穿鞋子的母亲看见了,一面清扫、一面反复唠叨:这些了尾仔,真浪费,这些了尾仔,真不知爱惜,还未穿坏,买了一双又一双…… 80年代前后,所谓的“免洗餐具”开始盛行,母亲看见随手丢弃的塑料碗、塑料杯、塑料袋、免洗筷,四散堆置,一大袋一大袋,经常感叹人怎么会变得这样浪费?一点点“捡拾”的习惯,都轻易抛弃。 我们自家不使用什么免洗餐具,平日对待客人、奉茶、吃饭或挑点心到田里,母亲坚持使用瓷碗、玻璃杯,或金属杯盘,宁愿花一点时间洗涤。 母亲一辈子劳动,总可以胜任,最痛苦的是面对时代的变迁,抗拒文明产品,引来不少嘲笑和数落,还要耗神耗力气面对我们不断的“据理抗争”。 母亲的固执、不合时宜,果真没有道理吗?作者:吴晟
帖间广告位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