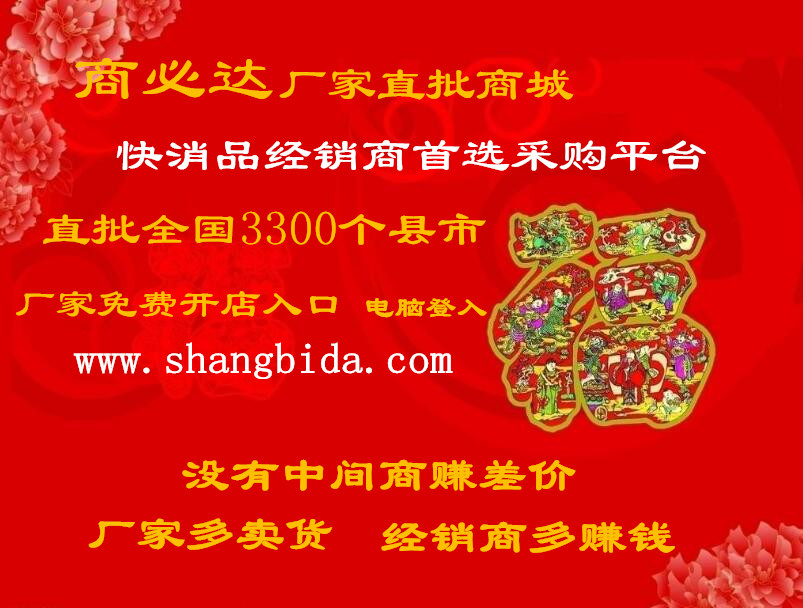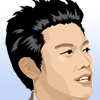远光灯的危害有多大?车灯的照明能力和晃眼能力就像卷在一起的灯芯紫霞和青霞,共生但矛盾——如果车灯的亮度越大,往往意味着会晃到别的司机的眼睛。目前普遍采用的四灯制式就是对这种矛盾的缓和,但还不能根治这种矛盾。
人眼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光学器件。我们看到物体,是由物体发出或反射的光线进入眼睛后,穿过晶状体在视网膜上成像。
但如果视野里存在一个强光源,它发出的光穿过眼睛后被眼睛里的屈光介质散射,散射光会在视网膜上形成一层“亮幕”,覆盖了周围事物在眼睛里的成像,我们就不再能看清周围物体;除非周围物体的亮度能超过这层“亮幕”才会被看到。
因而,有眩光时,往往可能让车子撞到周围的行人或静物等不发光的物体。
眼睛看到眩光时看不清东西,而在眩光之后,眼睛里也会出现局部盲点,需要时间恢复视力。随着炫光的强度增加,所需的恢复时间也增加。
一辆以100公里/小时速度行驶的汽车,在没有眩光的情况下,42米就能停下来;而远光灯的眩光让司机经过1.4秒才能看清东西,这时候车子前行79米后才能停下。如果79米处刚好有一辆车,一场车祸就会发生。
在各种眩光中,程度较严重的是“失能眩光”,干扰视力;最严重的是“目盲眩光”,过一段时间眼睛依然无法恢复视力。而程度不那么严重可以正常视物的强光,依旧会让人在心理上产生不舒服的感觉,持续性地暴露在这种亮光下,人更容易疲倦。
也就是说,经常暴露在远光灯下,有可能直接造成交通事故,也会让不断经受亮光的司机容易疲劳,间接带来的损失难以估量。
事实上,近光灯能照亮路前方大约50米的范围,这已经是半个街区的距离;远光灯则能照亮前方大约150米乃至300米远。一般认为,如果车速低于30公里/小时,近光灯的照明距离已经足够;超过30公里/小时时才需要使用远光灯。但在车流密集的地方,如果看不清前方,应该减速行驶,而不是打开远光灯。
在国外的经验规律是,如果车流变密集,远光灯使用量下降,甚至完全不使用。在20多年前德国的一项调查中,车流密集处德国司机几乎不会使用远光灯;在40多年前美国的一项调研中,如果每小时通过300辆,几乎没有司机使用远光灯;每小时通过200辆,则有10%使用;100辆,则有30%使用。
但这一规律不适用于中国人。2012年,有研究者调查了武汉5个繁华路口晚上9点到10点之间,平均每天每个路口在1个小时内有193.2辆车使用了远光灯。
还有研究者对苏州城区做了调查,发现有36条道路都存在违规使用远光灯和改装灯,比例达到20%。具体从其中6条道路做的调查来看,一个小时内这些道路的车辆通过量几乎都超过300辆,但仍有许多车违规使用远光灯。
但中国人不是唯一遍地“远光灯”的国家。印度人、阿拉伯人、秘鲁人等也爱开远光灯,不守交规。印度公路还因为其糟糕的路况、不良的交通管理、和人口众多,位列世界上公路最不安全的国家。
如果你去比较这些爱用远光灯的国家,你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道路照明不足。时至今日,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已经遥遥领先。NASA出品的夜晚地球光照图中,可以直观看出发达国家亮度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
而中国广袤土地上的灯光就要黯淡许多。即使在大城市密集的中国东部,中国的明亮度也赶不上东邻日本和欧洲北美。而整体来看,最明亮的国度可能是美国,其非城市地区的道路能凭借路灯的光连成一条亮线,线进而组成面,使美国东部几乎一半都是明亮的。
没有明亮的路灯直接决定了我们必须使用远光灯,而发达国家的道路亮度常能达到不需要使用的水平。
像苏州这样富庶又因为旅游业发达大搞城市建设的城市,其路灯数量在全国城市中高居第三,但在苏州科技大学的反复多次调研中,均有路段存在照明不均匀或不足的现象。
那为什么中国东部的经济和建设成就惊人,城市的明亮度却还是没跟上?这是因为道路照明的支出比我们想象的还高,在建设过程中还存在种种多出来的开销。
路灯装完之后的电费也是持久的花钱缺口。根据深圳市公开的市政数据,从2012年到2016年这5年间,其路灯用电量均超过20000千瓦时,平均达到24000千瓦时,如果按5毛每度电算,每年的路灯电费支出都上亿,还未考虑路灯、线路的维修费用。
高昂的支出让增加路灯、提升道路亮度需要多代的财富积累才能完成。美国道路照明的强势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美国人认为路灯可以减少犯罪率,而这种观念在美国建国之初就已有之,美国建国者之一杰斐逊就曾说过:“阳光可杀菌,路灯可防小偷。”
国内的道路建设则一再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在2006年的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中,中国是以城市级别来区分道路亮度,直到2015年新修订的《CJJ45-2015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才放弃了这种区分,并提升了次干道路的亮度。
中国参考英美等国家反复实验之后制定出来的《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以沥青路的主干道为例,平均照度应在20-30流明/平方米,约相当于白天照度的2-3%。但实际检测中照度常常达不到行业标准。
从统计数据来看,夜晚的车辆流量大约只有白天的1/4,但车祸多了50%;实验也表明,夜晚路灯的亮度能减少安全事故,但考虑到对生态的负面影响,路灯照明应控制在合适范围内。
相比起高昂的道路照明,道路规划可以用较低的成本一劳永逸地改善路况。一是给道路修建鲜明的路标,让司机减少照明需求;二是在道路中央修建绿化隔离带,可以减少车头灯对司机的干扰。
前者的案例是,在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一个叫多尔的妻子向她老公抱怨,高速公路对面开来的远光灯晃眼,下雨天车子容易滑到人行道,造成事故。听了妻子抱怨的老公多尔先生,发现给道路两侧刷肩线能减少车子跑偏,能减少交通事故,他就致力于带领他的基金会推广给道路两边刷白线。之后这一做法成为高速公路标配。
在道路中央修建绿化隔离带的提法早已有之。功能主义建筑泰斗勒·柯布西耶在提出现代城市的构想时,其中给城市修建快速路,就提出要在道路中央修建隔离带。中央隔离带分开上、下行车道,减轻对向行驶车的相互影响,包括眩光。
但修建中央隔离带面临着重重阻力,最主要的是城市空间的紧张,这在国内尤为严重。
一般国内城市将道路分为三级,分别是快速路、主干道和次干道,而在现行国标《GB 50220-1995 城市道路交通设计规范》中,规定快速路中央应当修建隔离带。在标准《CJJ37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中,进一步规定中央隔离带最小宽度是2米。
但在实际操作中常不被遵守。
改进照明和道路规划,是可以让司机自发减少远光灯使用或者减少违规使用的手段;但不经过一定的历史过程,国内无法做到。于是在可以预见的短期未来里,中国治理远光灯只剩下了一条路、也是最力不从心的一条路可走——惩罚乱开远光灯。
远光灯属于较难取证的交通违规,即使酿成事故也难证明。历史上戴安娜王妃的车祸身亡案中,一位目击者称见到一束强光使司机晃了眼,之后车子左摇右晃,才撞在了隧道石墙上。但当时经过车辆的灯光状况都已难判断,这一说法是否是酿成悲剧的原因之一未成定论。
事实上,能记录是否开了远光灯的监测设备至今主要出现在专利申请里,未曾广泛投入使用。国外出于民众对泄露隐私的担忧,反对给道路装过多监控。国内除了少数几个苦于远光灯乱象而试行“电子警察”的城市,其他城市主要靠抓现行治理乱开远光灯。但远光灯的使用通常是在晚上,交警已经减少;通常是在乡村路上,更少有交警管。
而且国内交通违规是在太多,酒驾、超速、闯红灯等才是抓查之重,这让乱开远光灯的司机大有侥幸心理。何况抓到了,惩罚也不算严重——如果没造成事故,只是罚款扣分;如果造成其他司机看不清而发生事故,还需要目击证人或者自己承认。根据相关判例来看,不会承担全责,甚至不到一半。
相对而言,在发达国家的交通违规处罚更严重。在新泽西州,2014年为没有及时关闭远光灯的罚单数是2618例,2015年是2453例。算下来,整个州平均每天大约有7例被抓到的,并不算高。他们与国内司机类似,会被罚款和扣分,但除此之外,发达的社会信用体系会有违规记录,次年需缴的车险费用可能会大涨。
当然,有了以上种种,只能说明中国人有爱开远光灯的软硬条件。使用远光灯本身不是它受到诟病的原因,在对面有车子驶来时依然不切换成近光灯,是真的没有礼貌而且危险。还有司机直接把近光灯也改成氙气大灯,让其亮度堪比远光灯,这样的司机和爱开远关灯的司机,没有什么两样。